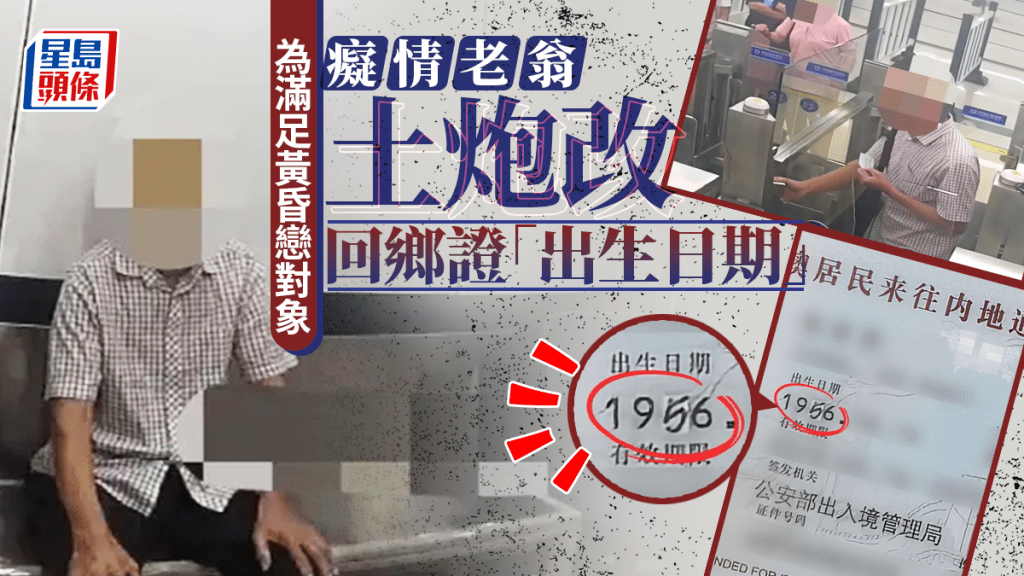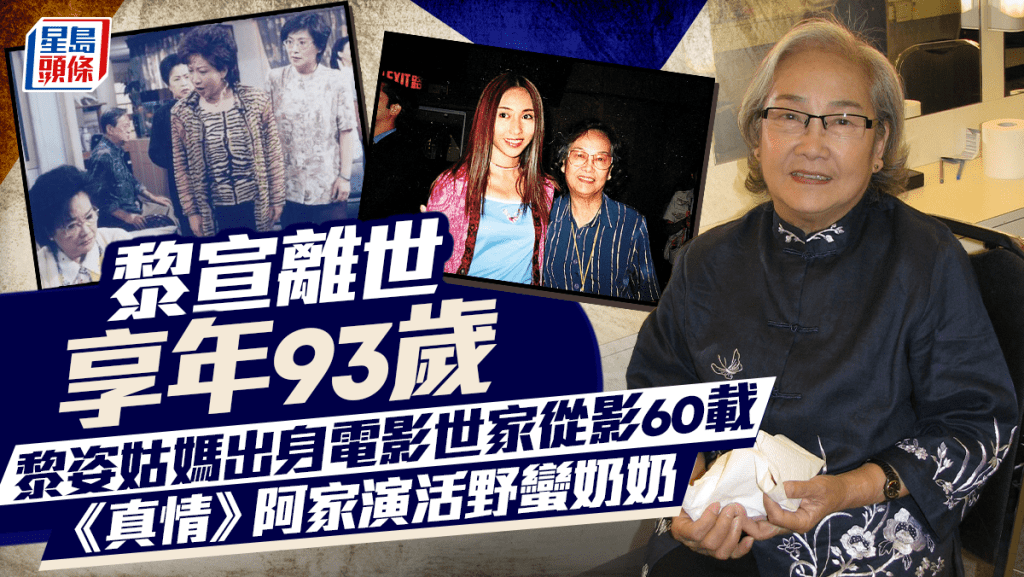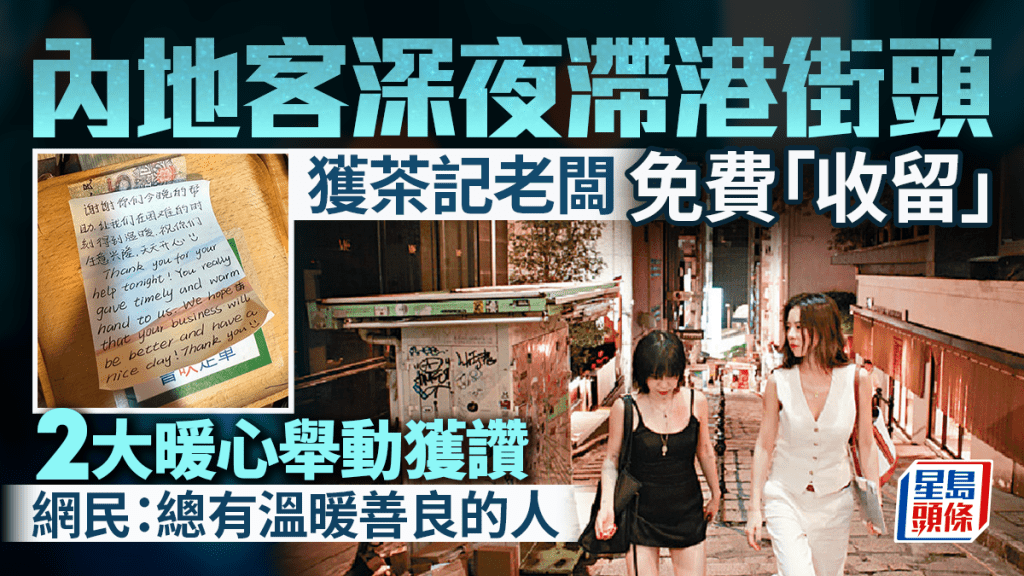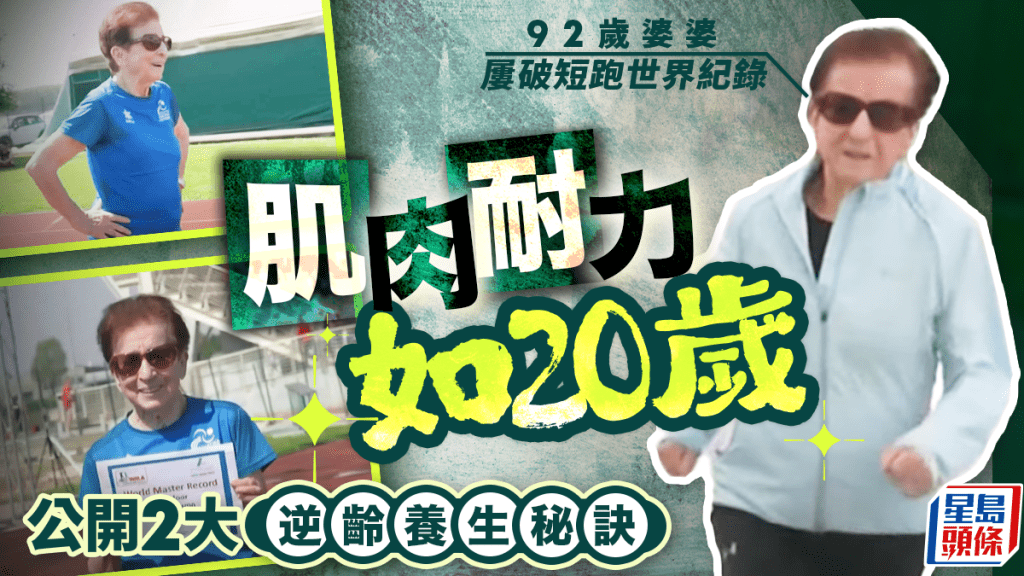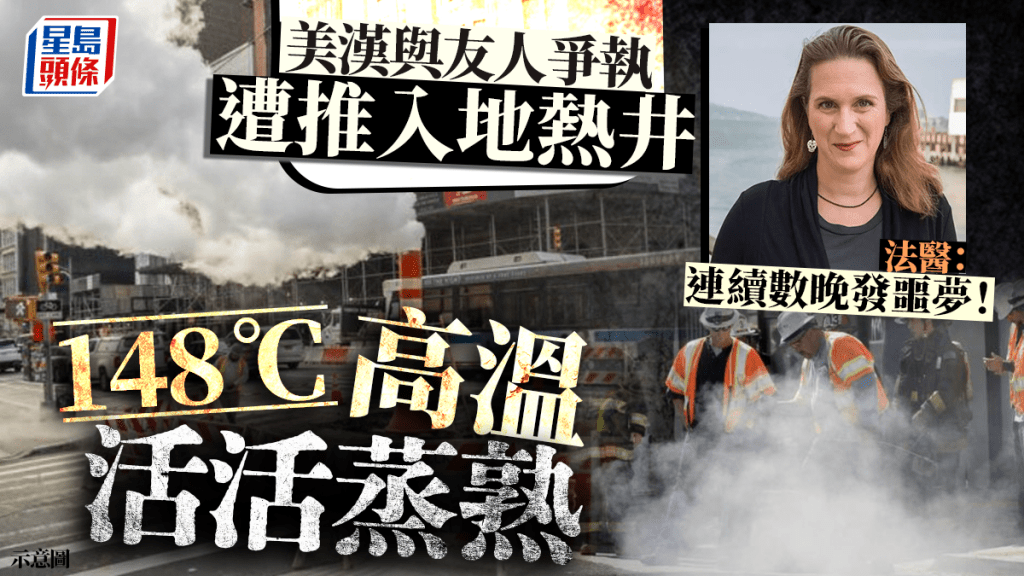黎諾維好奇發現新魚種「圓尾長鱸」
發佈時間:03:00 2025-08-28 HKT

香港三面環海,魚類生態多樣,惟大眾認識有限,懂得分辨養魚、海魚及觀賞魚,接觸面也多限於街市及金魚街。魚類學家黎諾維(Keith)自小對魚着迷,從一缸波子魚到遠赴台灣修讀水產養殖,再回港推廣海洋教育,出版《香港街市海魚圖鑑》,讓更多人認識「港魚」的故事。近日,他與兩名學者發表論文,記錄世界新魚種「圓尾長鱸」,為魚類界添一筆紀錄。他感恩從小已有明確的喜好及目標,在學習及研究路上有各方相助,才得以學有所成,回饋社會,盼將來仍然保持初心,為海洋出一分力。
細看那橙紅色的圓尾長鱸,尾鰭呈圓形,身上的縱紋連貫;與另一種相似的日本長鱸相比,後者身上縱紋具有白色鋸齒狀斑紋,兩者的背鰭鰭條及齒列數目均有異。Keith回想數年前在台灣讀書,有日於魚市場行逛,在芸芸眾魚中看到牠,說不上哪裏古怪,卻心存疑問,便買回實驗室看個究竟,結果測量各樣特徵後,發現該魚確是新種,「比對過很多近似種,許多特徵也對不上,便懷疑牠是世界新種,從未被發現。」
好奇心引領Keith踏上求真的道路,惟在學術期刊發表新魚種有基本門檻,結果邊讀書邊研究,歷經近3年努力,終在今年5月把成果刊登於國際期刊《魚類生物學雜誌》(Journal of Fish Biology),為魚類界添一筆紀錄。他坦言,背後工作量大,要釐清該魚種屬於哪一科、哪一屬,列明牠與其他魚種的不同特徵,並研究其全球分布性等。
赴台灣修讀水產養殖
Keith憶述,那時在基隆讀書,常到訪位於屏東的海洋生物博物館看標本,地理上一北一南,「每次去幾天,抓緊時間不停看標本及數據。」而要證明該魚種是獨立物種,便要確定獨有特徵,並非由變異或其他不穩定因素所致,更要有一定數量的「新魚」支撐,「我們找到12條,特徵十分明顯和穩定,跟其他類似的魚不同。」
在大眾眼中,發現、發表及命名新物種是大事,但在Keith的眼中,更重要是文化傳承,把魚的故事看得透徹,並且寫出魚在市場上的經濟和文化價值,「命名是保育和認識魚種的第一步。」他指,海洋有無數未知的物種,當未被看見,自然不會被調查、記錄和統整,或會隨年月消耗、過度捕魚、棲地被破壞等各項因素而消失。
文章備註寫上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內容,Keith相信,其論文不會是「圓尾長鱸」的唯一紀錄,別人會以其貢獻為本,豐富研究後再上一層,「這就是學術的意義。」他感恩與澳門魚類學家鄧志毅共同研究,並得到台灣學者、鰻魚界權威何宣慶教授的協助,才能順利發表文章。
事實上,香港亦曾發現世界新種,如香港鬥魚、香港後頜魚及葉唇笛鯛等。Keith直言,其手上尚有新魚種未發布,其中一條在本地街市發現,但因工作繁重,尚未有時間詳細研究及執筆。
因一缸波子魚從小明確喜好
Keith從小愛魚,兒時為一缸波子魚着迷,惟對魚的認識有限,只有在街市和金魚街接觸魚類。他憶述,自己曾在筆記寫下「日後想做賣魚的人」。旁人或會覺得他沒大志,但他認為,只是別人還未了解,「賣魚沒有問題,跟魚相關的行業,更有海洋學家及教育工作。」他坦言,也許自己內心也不清楚實際要做甚麼,但有明確目標,才得以引路至今。
他又言,中學時常到土瓜灣一觀賞魚店流連,該些魚來自德國或非洲,故晚飯後常到店內與老闆一同「接魚」,「牠們山長水遠到港,要慢慢適應水質、光度和落缸,做做下已經凌晨。」如是者,觀賞水族在Keith心中佔了一席位。
後來升讀高中,他已下定決心,以魚為學習目標和未來發展方向,並到台灣修讀水產養殖,「台灣的魚類產業大,海洋保育及教育體制亦較香港完整。」他指,課程以體驗式為主,如大學二年級要到養殖場實習,不論風吹雨打也要照顧魚類,「魚死就失去成果,打風要監測水質,寒流前要防範。」他續說,冬天仍要下魚池擦缸,故不可穿長袖衫褲及羽絨,不論多冷也穿拖鞋及短褲「出巡」,「冬天穿短褲和拖鞋的學生,必定是我們學系的。」
冀推動海洋教育熱情不變
「用興趣做主導的學習充滿熱誠。」他憶述,以往常在半夜駕電單車到全台北最大的批發魚市場「崁仔頂」,與漁販慢慢熟稔起來,到他碩士畢業時,與所有人都成為親近的朋友。他直言,在魚市場「打滾」是珍貴的體驗,「魚市場的實務知識不會寫在書本上,但漁販本身就是百科全書,有很多地方值得學習。」
「魚是我的動力和目標,身邊所有事也離不開魚;如果沒有魚,我的人生也頗苦悶。」訪問期間,Keith屢把感恩的心情掛在嘴邊,「原來從小到大有一樣這麼熱愛的興趣,貫徹始終,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
他直言,自己曾害怕對魚類的愛遞減,「工作總會感到疲憊,有日不喜歡魚就大鑊了!」猶幸其熱情未減,現時從事教育工作,亦會在餘暇推動海洋教育。他笑指,不敢想像失去魚的生活,寄語10年後的自己勿忘初心,仍然感恩,「我要記得這是一份恩典,記得為何要做海洋教育……希望不論10年、20年、30年,我仍有動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