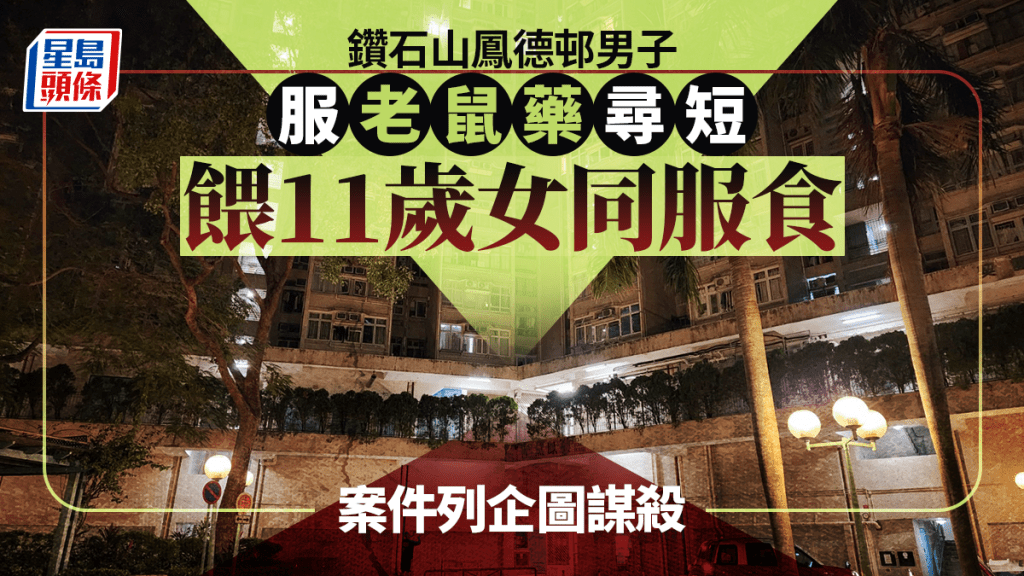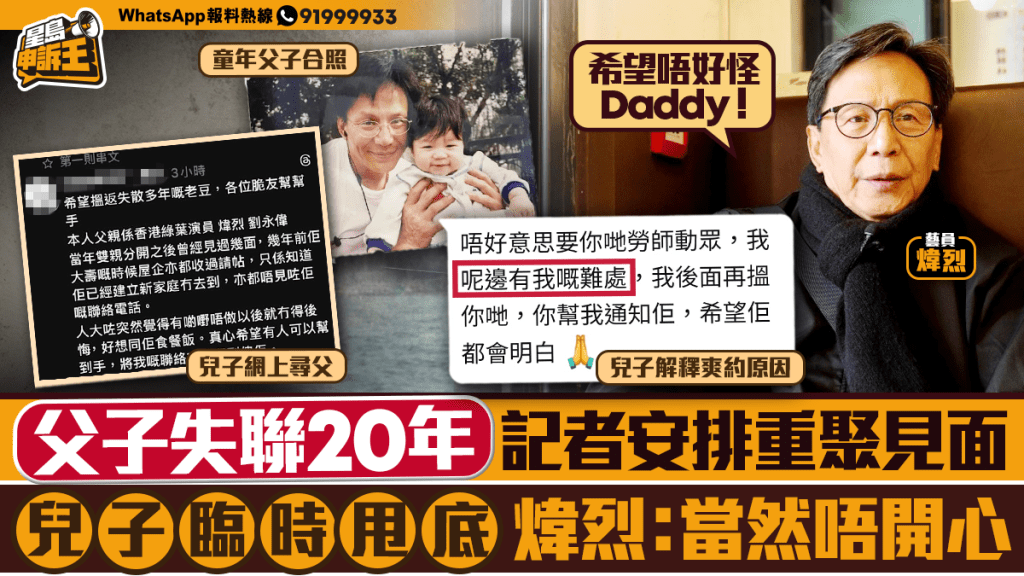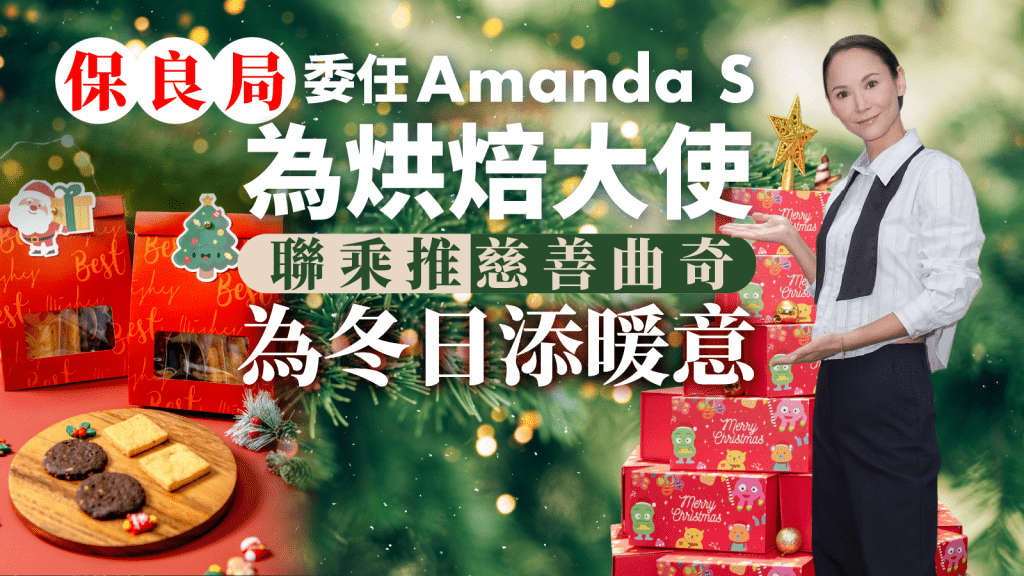淡水的戰略棋局:中國經濟命脈與科技雄心「隱形天花板」|陳新燊
發佈時間:08:00 2025-11-24 HKT

中國經濟總量穩步跨越130萬億元大關,全社會的聚光燈都瘋狂追逐芯片制程向埃米級的極限突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指數級疊代,以及新質生產力重塑全球產業鏈的宏大敘事時,一個古老、沉默卻致命的變量,正在暗處重新對中國未來的增長潛力進行更為苛刻的定價。
它不是流動的資本,不是稀缺的高端算力,而是文明最本質的物理基石——淡水。
長期以來,在主流經濟學家的增長模型中,淡水往往被簡化為一種取之不盡的公共品,或是邊際成本近乎為零的自然饋贈。但在2025年的深秋,當我們剝離繁榮的表象,重新審視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底層邏輯時,必須承認一個殘酷的事實:淡水資源,已從單純的環境外部性問題,演變為決定中國未來30年增長高度的「硬約束」。
世界銀行曾在十年前預警,水危機可能導致中國GDP損失2.3%。而根據最新的宏觀模型推演,若不進行結構性的供給側改革,至2050年,部分核心工業區和糧食主產區因缺水導致的GDP潛在損失可能攀升至2%至10%。這不僅意味數萬億元的財富蒸發,更是對中國經濟韌性的極限施壓。當芯片製造廠、AI智算中心、新能源基地等「新質生產力」在神州大地上拔地而起時,它們正迎頭撞上一堵看不見的「水牆」。
一、安全困境:正在收緊的三重死結
淡水資源的短缺並非線性的漸變過程,而是呈現出系統性的非線性臨界特徵。在當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經濟環境下,糧食、能源與社會穩定這三大國家安全支柱,正被水資源危機同步鎖定,形成了一個難以解開的「三角困境」。
首先,糧食安全的「地質代價」已觸及紅線。中國以全球6%的淡水資源養活了近20%的人口,這一農業奇跡的背後,是華北平原巨大的生態透支。這裏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區,面積約7萬平方公里。清華大學與地質部門的長期監測數據顯示,該區域淺層地下水平均埋深已顯著下降。在河北、河南的局部地區,累計水位下降逾百米,年地面沉降速率驚人。
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意味我們不僅是在抽取千百年來積攢的「地質存款」,更是在透支未來的基礎設施安全。當京滬高鐵、南水北調幹渠、地下輸油管道面臨地面沉降帶來的結構性威脅時,糧食安全問題已異化為地質災難與基礎設施風險。其隱性修復成本(Shadow Cost)遠超糧食本身的產值,這種「負外部性」的累積,正在侵蝕農業經濟的根基。
其次,能源安全陷入了「水-能-碳」的死循環。在「雙碳」戰略的深水區,能源結構正在劇變,但水的制約往往被決策者低估。火電依然是電網調峰的壓艙石,但其冷卻用水強度極高。更致命的是,中國煤炭資源九成集中在「富煤貧水」的北方與西北,這種資源錯配導致了極高的輸送成本與生態壓力。
與此同時,清潔能源也並非萬無一失。2022年四川的極端乾旱導致水電出力腰斬,全球電子與電解鋁供應鏈瞬間休克,這一「黑天鵝」事件警示我們:水已成為電力系統背後最隱蔽、最致命的變量。水、電、碳三者已形成一個複雜的死結,任何一方的波動都將通過產業鏈傳導,引發系統性震盪。未來的能源安全,本質上是水資源保障能力的競爭。
最後,社會穩定的「水基尼系數」不容忽視。水資源分配的不均正在加劇區域撕裂。北京人均水資源量僅為國際極度缺水標準的五分之一;而在西北部分欠發達地區,日人均生活用水遠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推薦標準。這種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用水差距,正在從單純的經濟發展差異,演化為潛在的社會治理風險。當「生態移民」從學術概念變為必須執行的行政命令時,其背後的財政轉移支付與社會治理成本將難以估量。水資源的公平分配,已成為衡量社會公平正義的一把新標尺。
二、產業變局:新舊動能同時撞上「水牆」
產業轉移與數字經濟作為中國經濟的兩大增長引擎,正同時撞上淡水資源的「天花板」。這不僅是地理布局的挑戰,更是產業經濟學的重構。
傳統產業的南遷,是一場昂貴的資本博弈。近年來,為了緩解北方環保與資源壓力,大量重化工業向沿海或南方轉移。然而,這並非簡單的物理搬遷。以鋼鐵產能南遷為例,除了廠房設備的移動,必須配套建設大規模的海水淡化廠及複雜的取排水系統。這筆隱性的水務基礎設施投資,往往輕鬆突破數百億元,顯著拉低了項目的內部收益率。
在新的產業版圖中,水資源保障能力已取代土地優惠和稅收減免,成為產業轉移成敗的關鍵前置條件。很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時,往往只算了GDP的產出賬,卻忽略了水資源的資本開支賬,導致項目落地後因水源不足而陷入「休克」。這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在水資源約束下,產業布局的最優解究竟在哪裏?
更為緊迫且具有時代特徵的,是人工智能的「水冷困境」。在AI大模型狂飆突進的2025年,算力即國力。但算力的物理本質是能量與熱量的交換,而水是目前最高效的冷卻介質。數據令人咋舌:一個中型智算中心的日均用水量可比肩一個數萬人口的小鎮;訓練一次GPT-5級別的模型,其冷卻用水量以百萬升計。
目前,中國相當比例的算力設施仍布局在水資源相對脆弱的區域(如「東數西算」中的部分西部節點)。這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戰略悖論:我們在用最稀缺的水,去換取最先進的智能。
當乾旱來襲,是優先保障居民用水,還是保障數據中心運行?這不再是科幻小說中的倫理題,而是即將擺在地方主官面前的行政題。算力競爭,正在悄然轉化為對淡水資源的爭奪。未來的科技戰,或許不會爆發在矽片上,而會爆發在水庫旁。如果無法解決高能耗計算的水冷問題,中國的AI雄心將被物理過熱所熔斷。
三、制度之困:誰在阻礙水的流動
技術並非不可逾越,真正的壁壘在於制度與結構。水資源之所以成為瓶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沒有被當作一種「資產」來有效管理,而是被困在行政分割與價格扭曲的牢籠中。
首先是財政天花板下的價格扭曲。農業用水長期佔據中國用水總量的六成以上,但其水價改革卻步履維艱。試點經驗表明,微小的價格上調都會導致農業成本的顯著攀升,進而推高CPI,最終需要財政進行精準補貼。這是一個典型的財政兩難:不提價,水資源浪費無法遏制,邊際效用遞減;提價,則觸動農業根本,最終需要財政兜底。若全面推行市場化水價,補貼規模將迅速突破千億級,這是當前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之重。如何設計一套既能反映稀缺性又能保障基本生存權的價格機制,是改革的核心難題。
其次是「九龍治水」的數據孤島。智慧水網被視為提升效率的良方,但現實中卻面臨嚴重的體制性障礙。水利、自然資源、住建、農業、生態環境等部門,各有各的數據標準,各有各的管轄範圍。數據不共享、標準不統一,導致所謂的「智慧水網」往往淪為一個個孤立的數字化大屏,難以實現跨流域、跨部門的實時調度與優化。沒有統一的數據底座,就不可能有高效的資源配置。這種信息不對稱,直接導致了水資源的錯配與浪費。
再者是跨境調水的地緣幻象。社會上常有「引貝加爾湖水」或「開發雅魯藏布江」的宏大設想。從工程經濟學與金融角度看,這些多屬於缺乏可行性的「幻象」。貝加爾湖調水面臨俄羅斯法律壁壘與覆複雜的國際地緣政治博弈;雅魯藏布江調水則需面對超長輸水距離、巨額海拔抬升帶來的能耗,以及國際河流的生態紅線。其單位輸水成本,將遠高於「海水淡化+合理半徑輸水」的邊際成本。
相比之下,1965年啟動的東深供水工程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本。60年來,廣東累計向香港輸送淡水逾300億立方米。特別是近期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的通水,實現了對香港水源切換的快速響應能力。這一案例表明,真正的水安全解決方案,絕非單一的土木工程,而是「政治互信+工程冗餘+金融結算」的系統性產物。香港為此支付了不菲的水費,但也獲得了全球頂級的供水安全保障。這才是水務作為「特殊商品」的正確打開方式——用市場化的契約,鎖定戰略性的安全。
四、破局之路:從達摩克利斯之劍到藍色基石
面對這一隱形天花板,我們需要的不是修修補補,而是系統性的重構。我們需要一場關於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水從被動的環境要素,轉化為主動的經濟資產。
第一,海水淡化需實現從「點」到「面」的工業化突圍。海水淡化技術已不再神秘,成本也已降至可接受區間。但要實現規模化替代,需翻越三座大山:
一是能源鎖定,必須與海上風電、核電等清潔能源深度耦合,解決高能耗與碳足跡問題,實現「水-能」互補;二是生態風險,濃鹽水的排放需通過深海擴散或鹽化工產業鏈消化,避免近海生態死區;三是輸水半徑,確立「沿海生產、梯級輸送」的合理半徑,解決內陸高程使用的成本公平性問題。
目標應是在2030年前後,將海水淡化產能提升至千萬噸量級,使其成為沿海工業帶的「標配」水源,從而置換出寶貴的淡水資源用於內陸生態修覆。
第二,推行水權交易,讓每一滴水都有價格。最大的障礙不是技術,而是利益格局。必須打破部門牆,建立全國統一的水權交易市場。這需要跨越三道門檻:清晰的產權界定、第三方效應的量化、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只有當水權像碳排放權一樣可以流轉、抵押、交易時,節水技術才會真正有利可圖,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才能發揮調節作用。例如,可以讓高耗水的AI數據中心向農業節水項目購買水權,實現資金反哺農業,水資源流向高附加值產業的雙贏。這不僅是資源的優化配置,更是財富的二次分配。
第三,創新水金融,重構風險與收益。水利項目投資大、周期長、回報低,社會資本往往「看得見、進不去」。破局的關鍵在於金融工具的創新。需要重新設計水務REITs(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以及專項債的風險共擔機制。例如,將水務項目的收益權證券化,讓保險資金、養老金等長線資金得以進入,將公共品轉化為可投資的優質資產。同時,開發「水資源指數」相關的衍生品,幫助企業對沖水價波動風險。只有打通金融血脈,水務行業才能擺脫對財政補貼的依賴,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環。
結語:把天花板變成地板
南水北調工程累計投資逾5000億元,為華北爭取了寶貴的緩沖期。但這本質上是用空間換時間,而非根治結構性缺水。真正的系統性破局,必須同步推進三條主線:建立「合理提價+精準補貼」的價格機制;構建「水權交易+金融工具」的市場體系;形成「跨流域調水+海水淡化+區域備用水源」的物理布局。
如果能在未來幾年內,實現萬元GDP用水量再降50%,並打通水務與資本市場的任督二脈,那麼水資源有望從懸在中國經濟頭上的利劍,轉變為支撐綠色增長與科技雄心的堅實基石。這不僅是一場資源的保衛戰,更是一場關於國家發展權與生存空間的戰略突圍。
在這場關乎國運的棋局中,淡水不再是配角,它是棋盤本身。
後記:致敬先行者
筆者曾在中信(香港集團)有限公司任職多年,擔任副董事總經理。有幸2006年12月,中信與本人在香港共同發起成立Citic Arabia Limited(中信阿拉伯有限公司),各佔50%股份。其後數年間,我多次往返中東,參與並見證了中國企業在海水淡化項目與相關金融安排上的早期探索,遺憾的是因時機未成熟而未能如願。但如今欣喜見證,中信和其他中資企業已在國內外成功落地多個淡水項目——這不僅是企業自身的成長蛻變,更是中國水技術走向世界的生動縮影。
謹以此文,致敬當年中信集團的領導與同仁,也致敬所有仍在實驗室、車間、招股書和鉆井平台上為每一滴水較勁的人。願我們早日把行業「天花板」變成後來者的「地板」,讓他們在更遼闊的賽道上,繼續把中國水技術的故事寫深、寫遠。
作者簡介:資深金融人
現任全國資產管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