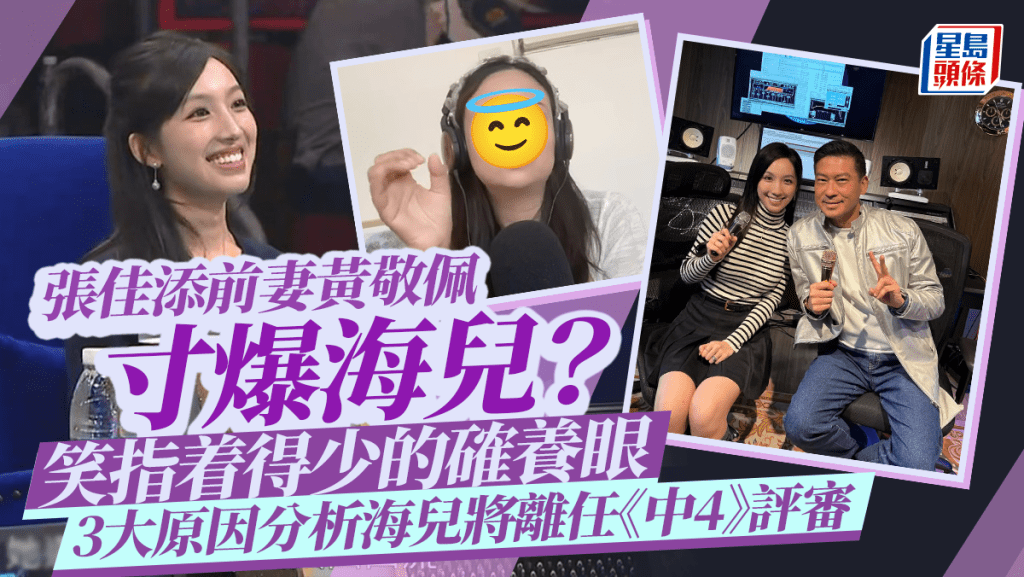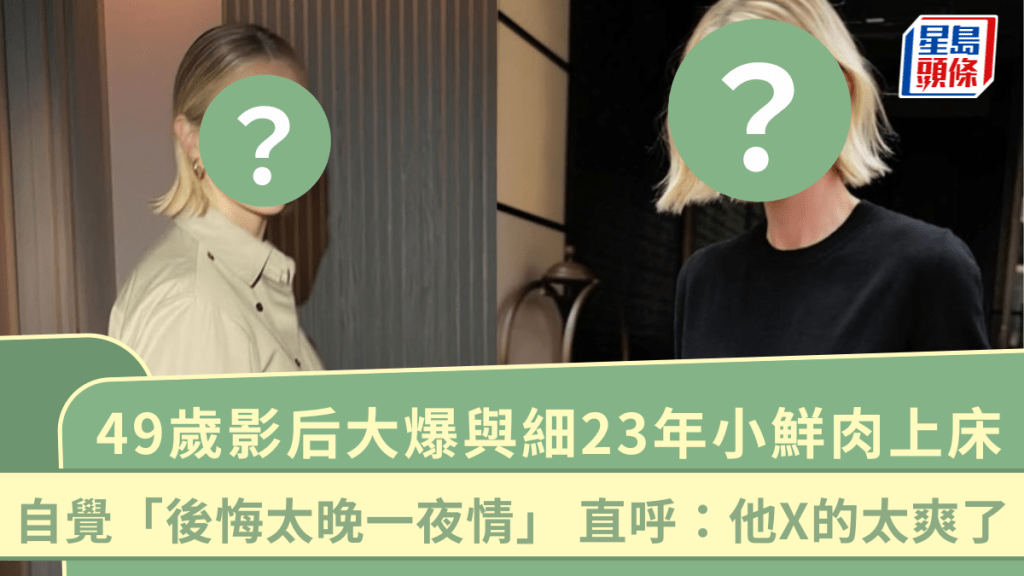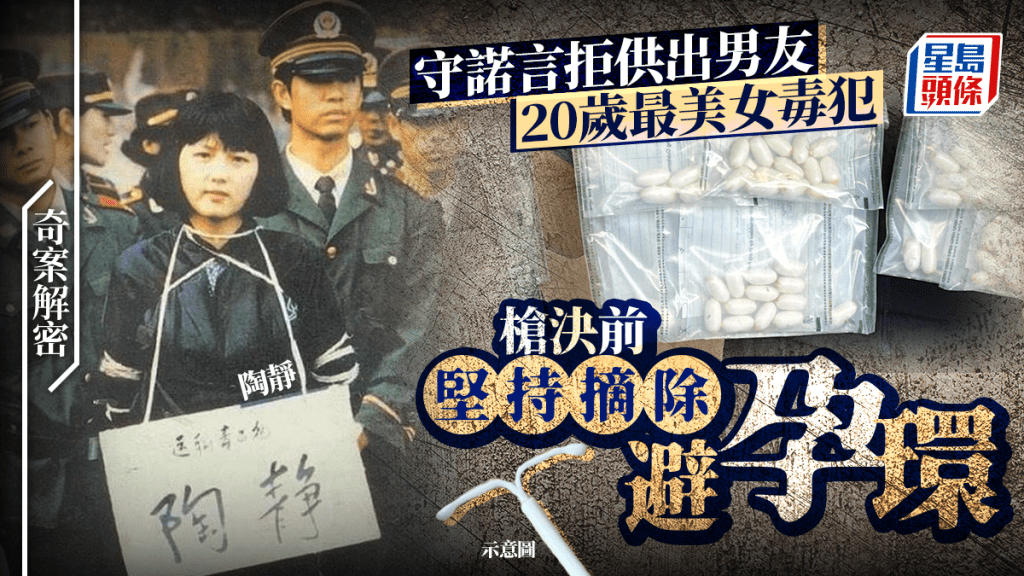情農荔枝窩12載 羅惠儀種出共生路
發佈時間:03:00 2025-07-07 HKT

荔枝窩,位於新界東北一隅,曾是繁盛的客家村落。隨着大批村民在上世紀中期移居海外,村屋荒廢、田地荒蕪。2012年,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副總監羅惠儀懷孕5個月時首次踏足村中,眼前是一片被雜草覆蓋的梯田與斑駁老屋。她不說「復村」,因為村落從未真正消失;她想做的,是讓人與土地重新建立關係。在其推動下,村中復耕農田、引入農林間作、修復村屋、重現米田與「米魚」生態,讓客家文化得以在當代延續與轉化。
「我很少用『復村』一詞,因為村落從來都在。」羅惠儀認為,「復村」容易讓人以為要複製往昔,「村的精神、社群的連結仍然在,村民移居英國,也依然覺得自己是荔枝窩村民。」在她眼中,荔枝窩不需要「復活」,她想做的,是讓被封鎖的資源得以重新活用。
荔枝窩村位於新界東北區的偏遠郊野,毗鄰船灣郊野公園和印洲塘海岸公園,由客家曾、黃兩氏於300多年前創建,他們將山坡切割成梯田,進行耕作,最高峰時期有逾千人居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落後山的天然樹林被視為風水林,具保護村落及調節微氣候作用,加上海岸有大片紅樹林,成天然避風港。大部分村民在1950至1970年代移居至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其餘則搬至市區居住,村落隨歲月荒蕪。
「讓人與土地重建關係」
2012年,羅惠儀懷孕5個月時,首次到荔枝窩考察,田埂全被雜草吞沒,野草層層疊疊,村屋的外牆斑駁、門板斜垮,保留了原始風貌。她指,村落被郊野公園包圍,屬「不包括土地」,政策上禁止開發,限制村落發展,卻也保護這塊風水寶地,「我們也曾擔心活化後被收地,但在這裏我們有條件尋找更多可能性。」
活化老村,並非要創造新的主題樂園,而是讓人與土地重新建立關係。農是荔枝窩村的重要元素,港大團隊與村民、綠田園基金、長春社和香港鄉郊基金合作,其中綠田園重新開墾農田。羅惠儀與團隊向村民租地,在村中試驗復耕,種的不是幾畦菜心或西洋菜那麼簡單,而是引入「農林間作」理念,把林地與農作結合,保留原有大樹,在林蔭下種植咖啡,咖啡下種薑,樹蔭外種冬瓜,「我們想做的是高增值農業。」
港大團隊在沙頭角建立食品加工廠,將農產品升級成為醬料,如雙薑黃金醬、冬瓜露等,更與本地酒廠合研薑味氈酒等。她們也鼓勵村民成立社企「暖窩」,也是為了促進荔枝窩的可持續發展,方便日後村民與其他機構合作。
她坦言,偏遠地區種傳統蔬菜無競爭力,團隊希望避免大規模砍伐原有林木和過度開發水源,在保護生態下,發展出可持續的農業模式,「資助總有完結的一天,村落有自己的經濟模式,才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搭橋修路 風水林環抱村落
團隊也邀請專家搭橋修路,並以客家中式建屋技術,就地取材利用荔枝窩的沙泥、禾稈和蠔殼等修復了村口相連的舊村屋。村中處處是歷史事,如從西門進入村落的小徑,被荔枝窩村民稱為「新娘路」。根據村中習俗,新娘初嫁入村的1至2周,只能從西門進出,待被接納為「自己人」才可走東門。
現時「新娘路」兩側,已恢復為一整片米田。羅惠儀說,米田還棲息着本地原生的「米魚」,該魚對水質和環境有要求,已在荔枝窩消失多年,團隊找學者協助從鎖羅盤重新引入魚苗,在新復耕的稻田中繁衍。她最喜歡停留於該地,「站在這裏,你會聽到河溪的聲音,眼前是米田,遠處是村屋,再後面是風水林,風水林環抱整條村落。」
「要所有村民回來住並不現實。」她說,團隊的策略很簡單,讓村落有些「人氣」,非指觀光人流,而是在這裏留宿、生活,能夠互相照應的人,「晚上若頭暈身㷫,有人可以幫忙,才會安心留下。」
這些年來,村中出現了不少「新居民」,有藝術家、有農夫,也有退休人士來此養老,「有些人一星期來住3晚,有些人乾脆搬進來住。」她特別提到作家兼藝術家葉曉文,最初以壁畫創作進村,後來申請資助種起食用花,開設工作坊,教小朋友採花、做曲奇、製作「花花」雪條,「她不是客家人,但她很喜歡這裏,現在一星期有4至5天都住在這裏。」
昔日村民甚少回村,自活化以來,回村頻率大有提升。背後功臣之一的羅惠儀卻不敢居功,她說,做這些項目,沒有人會當作一份普通的「工作」,「你要和村民、和不同的人打好交情,真的把他們當朋友、當親人。」
「荔枝窩行得通 其他村都有希望」
她說得雲淡風輕,這樣的關係是用12年時間累積出來的信任。她和團隊不僅在村裏「上班」,也會在農曆新年來拜年、在關公誕一同參與拜神儀式。她的子女也熟悉荔枝窩,有時周末來到村裏,她忙着帶團考察,孩子就在村裏跑來跑去,「很難分得清哪些是工作、哪些是生活。這條村早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真的當自己是半個村民。」
羅惠儀過去甚少接受訪問,這次難得參與,因談的是客家元素,「我真的感受到客家和我的連結。」那種連結不只來自語言或食物,而是更深層的村落文化,「說來簡單,但其實是很沉澀的,裏面有很多東西。」
因母親是客家人,她小時候暑假幾乎在龍鼓灘的客家村落度過。她記得與外公捉馬蹄蟹,「今天想吃,就去捉一隻,不會多捉,是自然而然的共生方式。」
她指着田邊一株不起眼的野草,這種客家人稱為「布薑仔」的黃荊,也是她童年記憶的一部分,「小時候,老人家說嬰兒黃,就會拔這種野草來煲水,幫孩子洗澡。」她的孩子出生時,也延續了有關傳統。
該野草還有天然驅蚊的功效,有藝術家向村民了解故事後,研發出一系列天然蚊怕水。羅惠儀說,「這也是另類保存客家文化的方法,看以往村民如何就地取材,再將其作現代化地加以運用。」
荔枝窩並非本港唯一的客家村,也不該是唯一一條被活化的村落,羅惠儀說,「如果荔枝窩行得通,其他村都有希望。」她相信,除了以地產項目為主導,香港鄉村仍有更多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