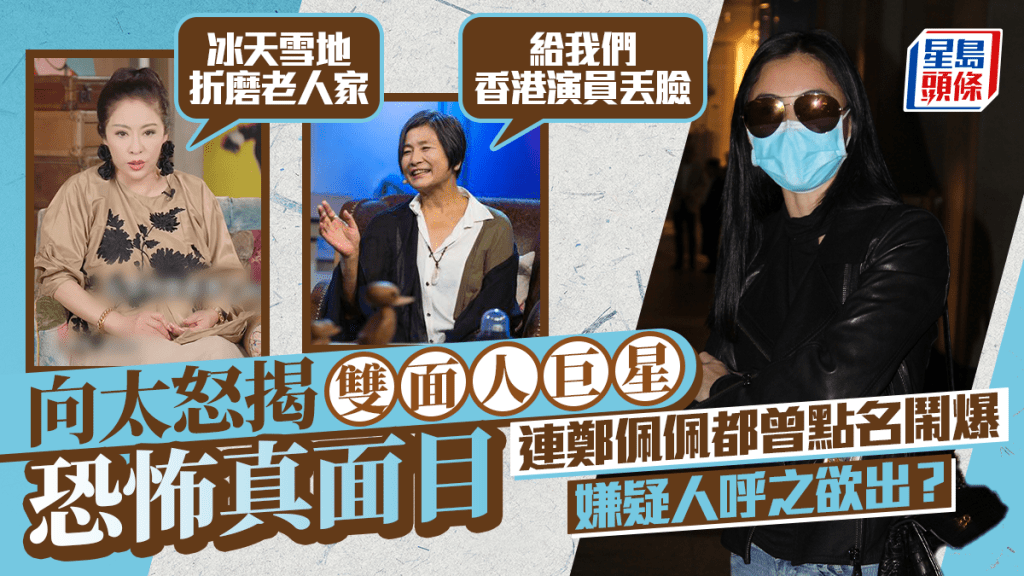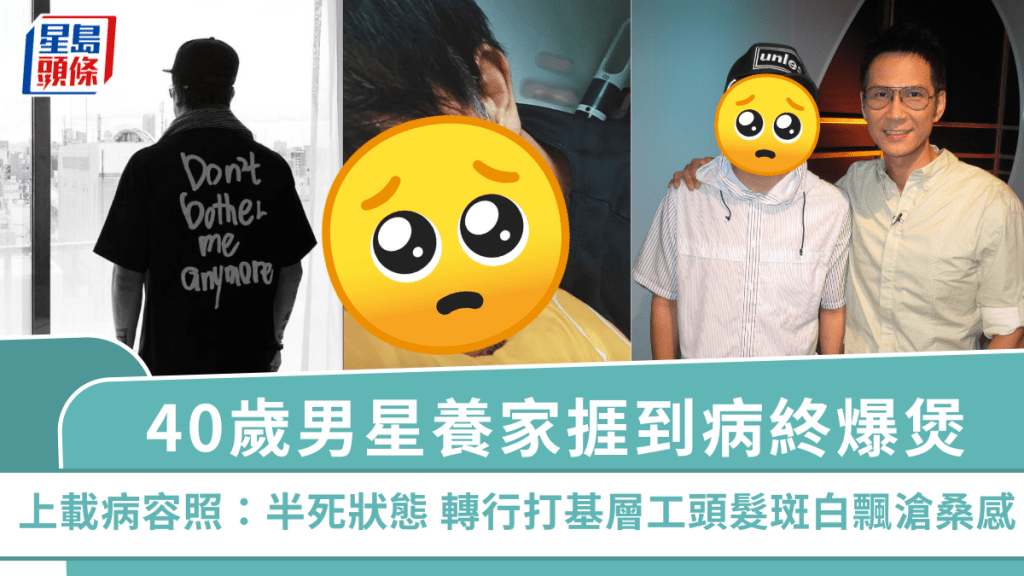嘉洛 - 由《宿劫》到《凶器》一次言之有物的考核 | 嘉洛的光影世界

今個暑假最具創意與可觀性的竟然是荷里活恐怖片,由《罪人們》到《凶器》,那種借生活上不安、恐懼諷刺美國社會的混亂與不確定性,較內地穿越劇集借古諷今來得高技巧與深度,確是令人驚喜。其中新晉導演札克克瑞格(Zach Cregger)連續兩部作品:由2022年編導的《宿劫》(Barbarian)到今年的《凶器》(Weapons),兩次均成功引發全球恐怖片迷熱烈討論,算是圓了一個新導演透過作品言之有物的考核。
對於恐怖片迷來說,《宿劫》堪稱當年驚喜之一,早段女主角租住Airbnb遇上連串危機,跟觀眾齊齊跌入連環殺人驚悚片疑雲當中,其後來一個大轉折,將故事推往另一方向去,最後又回到早段性別議題隱喻中。編導克瑞格要探討的是女性恐懼、母性
堅韌,對應男性傲慢、自大跟貪婪,處於同一場景下的分別,觀眾看到結局時才恍然大悟。影片亦側寫了美國政經發展、底特律由汽車大城一度破產,淪為全美最危險城市之一,種種問題在《宿劫》這恐怖片內呈現,並在娛樂性與社會諷刺之間取得平衡,儘管細節仍有沙石,但已是一次令影迷滿意的恐怖之旅。
到了今夏的《凶器》,克瑞格要探討的性別、社會議題及敘事結構,較前作《宿劫》更廣闊與完善。電影透過5個角色的章節,層層揭開17個失蹤兒童謎團。表面上是女巫作法的超現實失蹤事件,實際是批判當代槍械政策爭議、校園霸凌、家庭教育失衡、官僚作風等問題。《凶器》成功地營造出一種令人不安氛圍,即恐懼潛藏在生活上的不協調:如殭屍般父母被餵食、老師重壓下崩潰、唯一沒有被消失的孩子被逼成長,最後更須以巫術反擊,雖成功解除魔咒,但對所有小孩傷害已成,即創傷已是永
不可逆轉的命運。
克瑞格的《凶器》有着對先輩恐怕大師作品影子,由大衛連治的潛意識運用,但刻意避免完全解讀;尊卡本達對社會不安審視;還有大衛哥連堡對人性黑暗面關注等。3年內兩部作品,證明克瑞格已掌握銀幕上恐怖為何物的功力,令大家對其未來重啟《生化危機》系列有着信心,估計不會是簡單為求核突、官能刺激了事。
嘉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