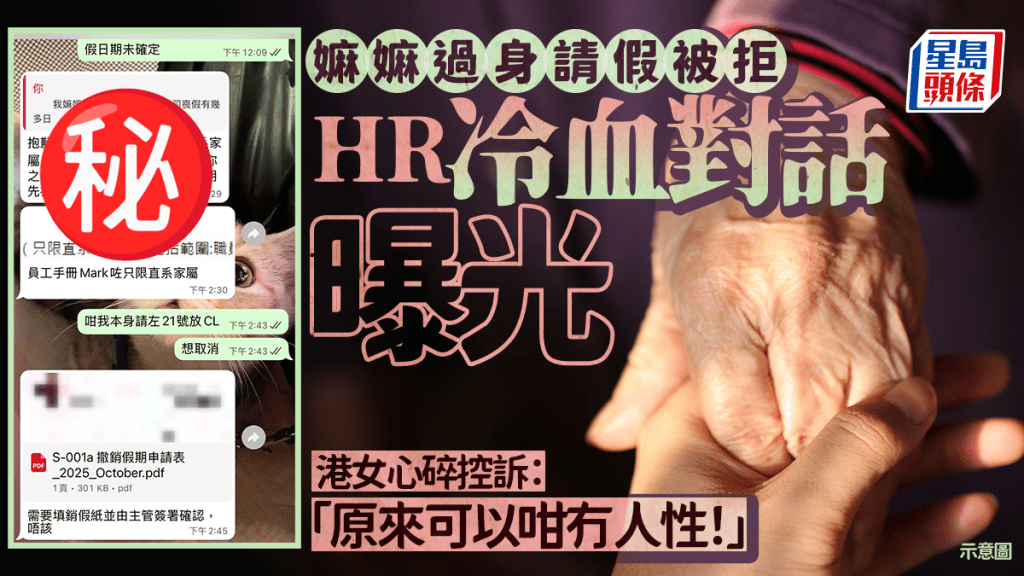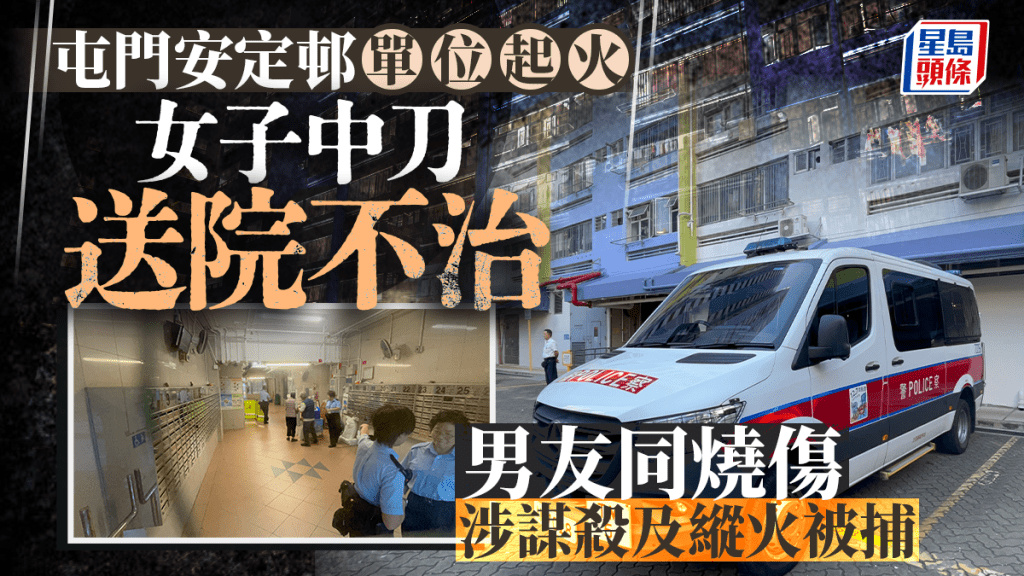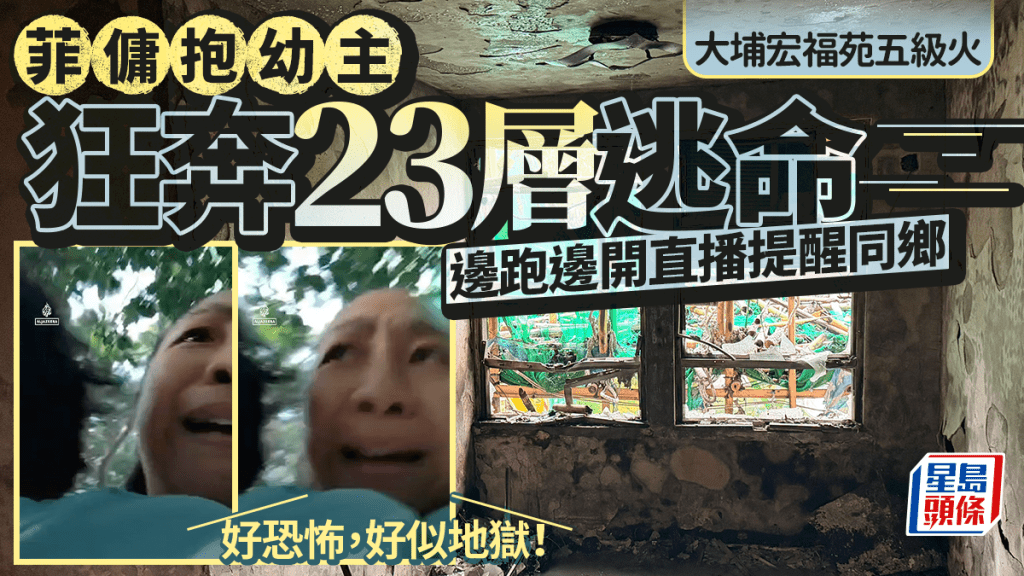「世界工廠」遷移?全球電子生產網絡重構下的博弈|嶺航未來
發佈時間:12:00 2025-08-03 HKT

隨着全球經濟環境和貿易政策的變化,「世界工廠」的角色逐漸從中國轉向東南亞地區。而中國內地的成本上升,勞工、環保等政策要求提升,加上貿易戰影響,促使電子製造商重新考慮其生產基地的選擇。
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因其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和穩定的投資環境,成為外資企業新的聚集地。筆者強調,「由中國到越南」並非單純的產業地理遷移,而是在全球化退潮、地緣政治博弈與區域經濟重構多重因素驅動下的複雜變革之結果。
企業與國家的雙向選擇

越南的成功乃依賴精心構建的制度環境和政策體系。當地通過模仿內地的成功經驗並提供優惠政策,吸引不少因中國政策變化而撤離的企業和世界各地的投資。同時,越南借力《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國際協定加強其制度吸引力,引進不同層級企業,如三星、英特爾、佳能等,以確立其新興電子製造樞紐的地位。
雖則越南已成為東南亞最大的電子出口國,其依賴外資快速嵌入全球生產網絡的模式也面臨風險。儘管本土企業參與度逐漸提升,其出口附加值仍遠低於中國甚至其他東南亞國家,使越南陷入「有增長無發展」的困境。這種「出口主導」模式若缺乏技術自主,可能會重蹈「組裝經濟」的覆轍,為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外資與培養本土技術之間的平衡提供了重要警示。
延伸閱讀:打造人機共融新模式 心理學研究助AI成積極協作者︱嶺航未來
由資本要素到地緣政治
在越南東南部和新興的紅河三角洲產業集群中,企業的轉移策略反映出全球生產網絡的權力結構。
例如,三星將其手機組裝產能集中於越南,但核心部件仍依賴隨之而遷移的供應商,或是來自日韓與中國的進口。研發環節則主要限於剛完工的河內三星電子研發中心。
縱使越南在其全球供應鏈中的一、二線供應商數量從2014年的25家增加到2022年的257家,但大部分本土企業仍限於組裝及製造低端配件,體現了「依附性增長」的脆弱。
另外,中國內地中小企業則展現出獨特的生存智慧。除了低調的「集群式遷移」以縮短和客戶的距離和避開政治風波外,部分供應商更主動將低端製造向外遷移,並在國內大力發展高端研發和自家品牌,由三、四線逐步躍升為一、二線供應商。這一轉變也反映了中國從「世界工廠」到「自主研發」的升級。
2018年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後,各大電子企業加速了「中國+1」的風險對沖策略,越南「漁翁得利」。而新冠疫情期間,內地的「清零」政策進一步使企業供應鏈策略從「效率優先」轉向「韌性/市場優先」,促使全球企業重新考量其生產基地和供應鏈布局。
延伸閱讀:探索「人機相長」概念 善用AI促進教與學體驗︱嶺航未來
對全球生產網絡的啟示
通過自2016年起的田野調查與跨國訪談,筆者與香港浸會大學楊春教授的新書《生產轉移至東南亞:21世紀以來電子跨國企業向越南遷移》以全球電子產業遷移至越南為例,揭示背後的複雜機制,並將2010年代末不同的風險加入分析,證明外部環境變化不容小覷。書中指出企業遷移是對大環境、區域稟賦、自身條件和網絡功能等因素變化的反應。越南靈活制訂政策實現「戰略耦合」,證明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制度創新主動創造生產網絡位置(和風險)。
同時,研究揭示不同企業與政府博弈的特徵和結果:國家層面通過法規爭取高端企業入駐,省級政府以服務和優惠吸引組裝環節,終使電子生產鏈能成功「落地」。
筆者強調,在全球戰略競爭與技術脫鈎的當下,全球生產網絡的未來將由發達國家的技術霸權、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彈性,以及跨國企業的策略選擇所共同塑造,並值得持續的關注。
本欄歡迎院校學者投稿,分享個人學術見解及研究成果,1400字為限,查詢及投稿請電郵︰[email protected]。
文:嶺南大學研究生院研究助理教授陳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