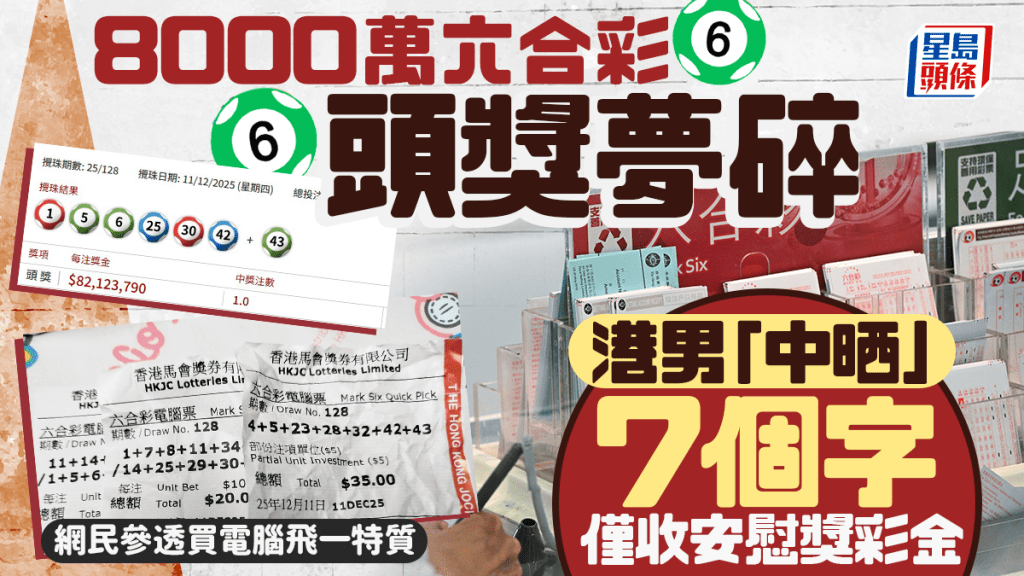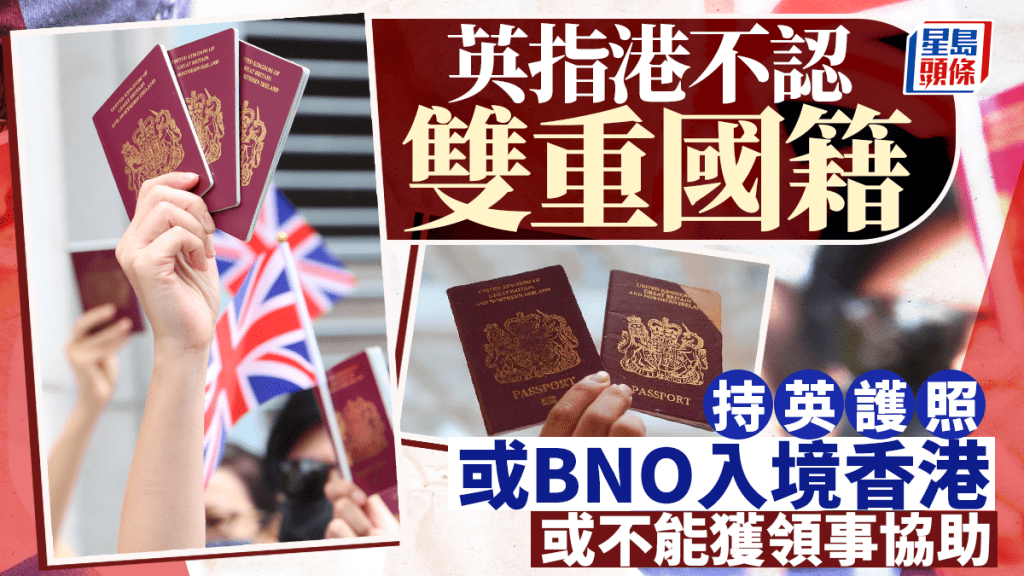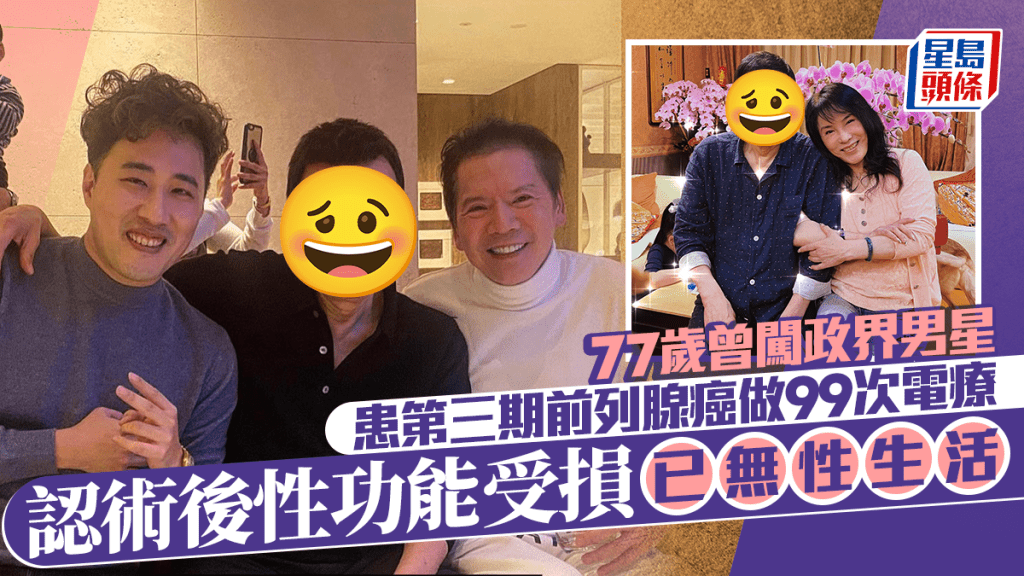外婆

在我有认知的日子,外婆已是家族中的长者,有著很崇高的地位。我们的家族庞大,亲戚众多,就只有母亲跟她相似。大概也是因这原故,外婆也好像跟我格外的合得来。
儿时家中的人重病,母亲便把我放在外婆家。外婆体力不够支付跟我一天的玩耍,不到半天便会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那时候便总爱趁她睡觉时把外婆的东西都收藏在床底下。看著外婆起床后性急的叫嚷著我便会乐透得上半天。年幼时外婆家境清贫,每天都只是些青菜豆腐。放在眼里我总会忍不住的告诉她:「总有一天,就在我找到工作以后,我便会带你吃一趟好的自助餐。」
这顿自助餐总算没有迟来。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便用了第一份工资买了音响设备和请了外婆在五星酒店饱吃了一顿。只是以后她改了素食,一起用膳的地方便都在斋菜馆了。外婆活到了九十多岁,也渐渐地患上了糖尿病、胆固醇和高血压。听力转差了,却不肯装上助听器。慢慢地活动时胸口会痛,走起路来会气促。因著这些心衰竭的征象也进了不少次医院。她的听力退化得厉害,我和家族中的年轻女士探望她的时候会不忘赞她说:「外婆你好叻!」她总是听不清楚以为人家在说她漂亮。「甚么?我不靓,你们年轻的才靓」说出来时还大声得整个病房也听到。护士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觉得有她在的日子病房也多添了点欢乐。
内科医生跟我说她是冠心病需要做心导管的手术。我们游说著外婆。老人家便有一套理论。「我都过了平均生存的年龄,手术的便用不著了。」我们轮流劝说着,就是连她的几个子女也是拿她没办法。面对著逐渐严重的病征,她好像还是跟平常一样,一样的活动,一样的生活,看不到半分的担心。日子便跟平常一样的过去。就在疫情爆发之前的春天,她跟父亲一样因肺炎引发的心衰竭在差不多的时间便离我了我们。我明白不了老人家的心态,总以为可以医治的便应该医治。只是看见她面对生死的云淡风轻,想起读医的理论和现实本来就有差别。没有病人会是完全的一样,原来医学从来都有其哲学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