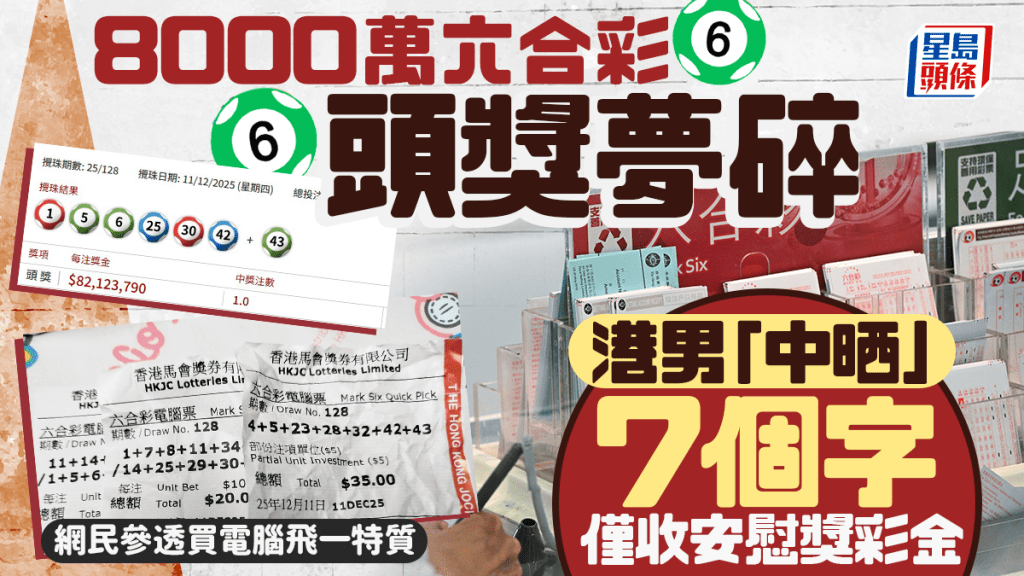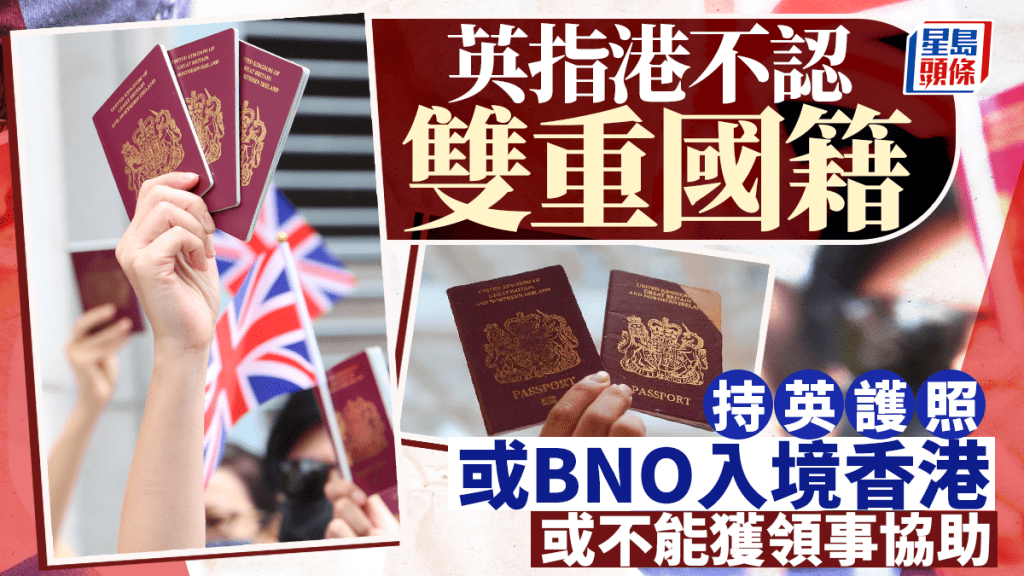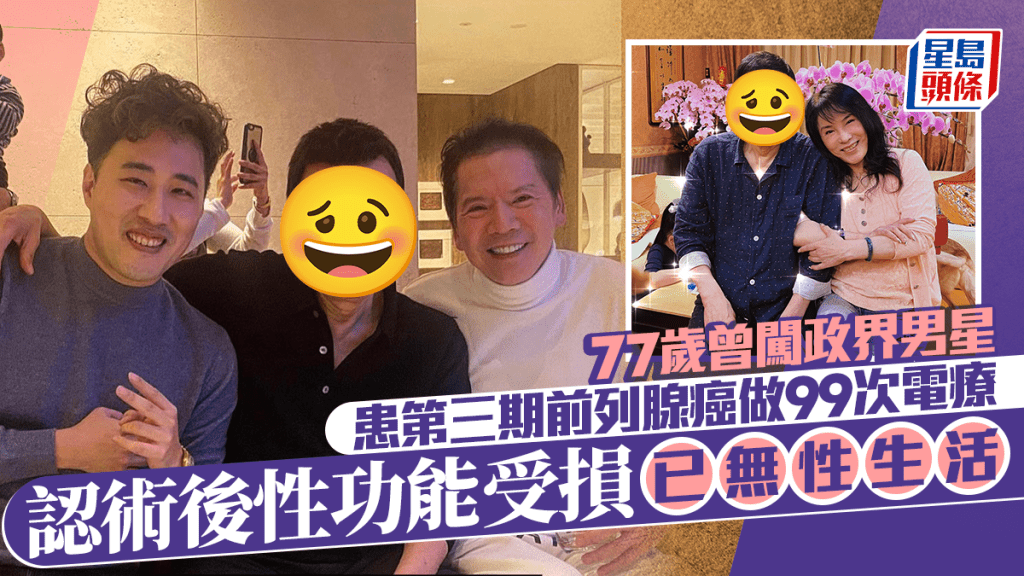喝酒

喝酒是穿肠刺肚的。它跟心脏病、中风、肥胖和很多癌症都有着关连。这是大部份医生都能说出来的道理。
大概医生也不是特别注重健康的一群。我认识的医生很多都颇会喝酒,有几个外科的甚至会在放工后喝个烂醉。他们会告诉你喝酒是一种纾缓压力的方法。
话这样说,我对喝酒的病人大多有丁点儿容忍。除非是喝得太过份,否则不会要求他们完全戒掉。当然喝得厉害时很大机会影响肝功能,又或是作电脑扫描时,会发现小脑轻微萎缩起来。我总喜欢运用著这些客观的报告作为劝解酗酒病人的工具。纵然如是,一般来说他们还是很难被劝服的。
晚餐时喝酒也是一种礼仪,经历过最讲究的那次是在苏格兰。那年参加了皇家内科医学会的周年大会,庆祝晚宴在一座古堡内进行。晚宴共五道菜,每道中间便会配上一杯特别设计的红酒。讽刺的是,那时的医学会主席已经喝得半醉,却还在演讲着说来年的计划是如何宣传教多些英国人把酒戒掉。
记忆中喝过最厉害的几次都是在海外。有一年被邀请到韩国出席演讲,会议前被带到一间地道的传统韩国馆子晚膳。甫坐下不久便已体会到韩国的饮食文化。原来食物并非重点,酒还是大碗大碗的给灌了上来。看著那些教授们千杯不醉的豪爽,跟平日的斯文形象截然不同。我不胜酒力,只好推说香港人不习惯喝太多。
最怀念是数年前在夏威夷参加好朋友的婚礼,婚礼前趁机跟朋友相聚。原本的提议是享受一下夏威夷的海滩和游泳,最后却变成在酒吧消耗了一整个晚上。我们提到读书时的回忆和理想,谈起同学们毕业后各散东西,和大学毕业那年在芝加哥喝醉酒说起已背叛了的理想而打了场架。说著说著便从夕阳谈到黑夜,然后又从黑夜谈回了天明。还相约以后还会再喝,想不到今年朋友已不在,那偶然的相聚原来已是最后的一次了。
那次之后我再没怎么喝醉。我想我们都对酒又爱又恨,大概是它也为我们背负了太多的回忆与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