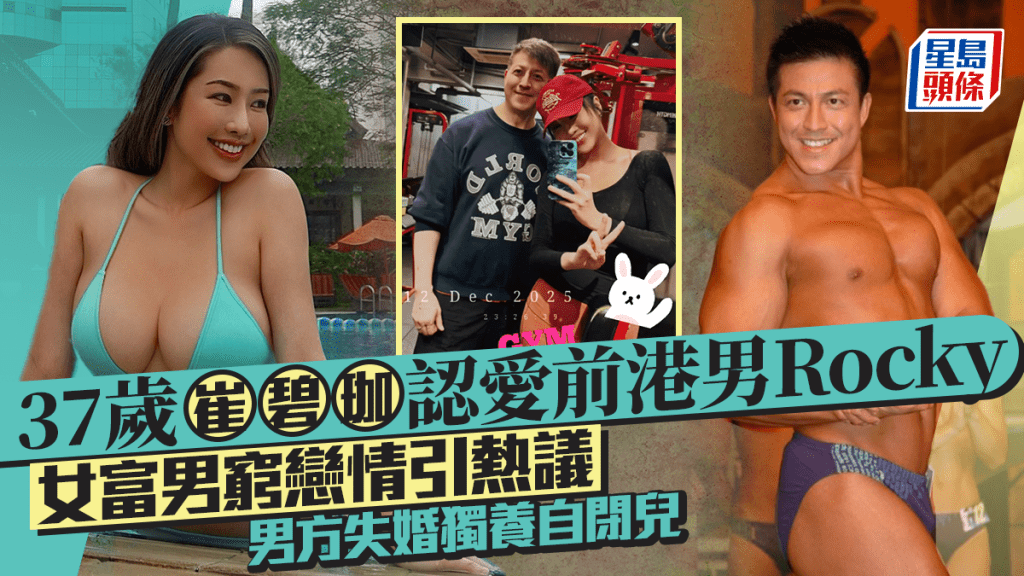父亲
父亲的柏金逊病是我离家多年才发现的。那天在街上心血来潮的看著他的碎步,才想起这读了多年的疾病原来早已存在自己的身旁。以后父亲的老人病便一个接一个,认知障碍、心律不正和中风。令人感慨著岁月真正的饶不过人。
跟其他柏金逊病患者一様父亲老是受著吸入性肺炎的缠绕。最后的几年他已是医院的常客。每次都是一种规律的疗程,氧气、盐水、抗生素,然后便是退烧离开医院,等待著下一个或数个月后的病发。父亲进院多了,大家便在电脑纪录上写上了是钟医生的父亲,好让每次住院也会能第一时间的通知我。
不停的肺炎后果便是肺部不可逆转的破坏。最后一次在内科病房父亲的右肺片已是蒙蒙的白成一片。同事问我想怎样处理,是非入侵性的呼吸机还是吗啡。明知是渺茫还是舍不得的上了呼吸机。于是剩下来的一个多星期便都是机器声和老人家的呻吟声。我难过的牵著他手,他却是认不出自已的儿子还只会重复的说著「辛苦,真的很辛苦。」最后那天他的肺部状况连呼吸机也支持不来,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把最后的一丝生命都给呼走了。我哭得伤心,把面罩换了一个又一个,后悔著从来没想过把他的呼吸机换成了吗啡。
多年以后我还总是梦著父亲。那天早上家里飞进了蝴蝶,母亲说是父亲来探望。内心感触,便想起了最后那晚上的一幕。大概以后也不愿再给自己的家人作医疗的决定。
最H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