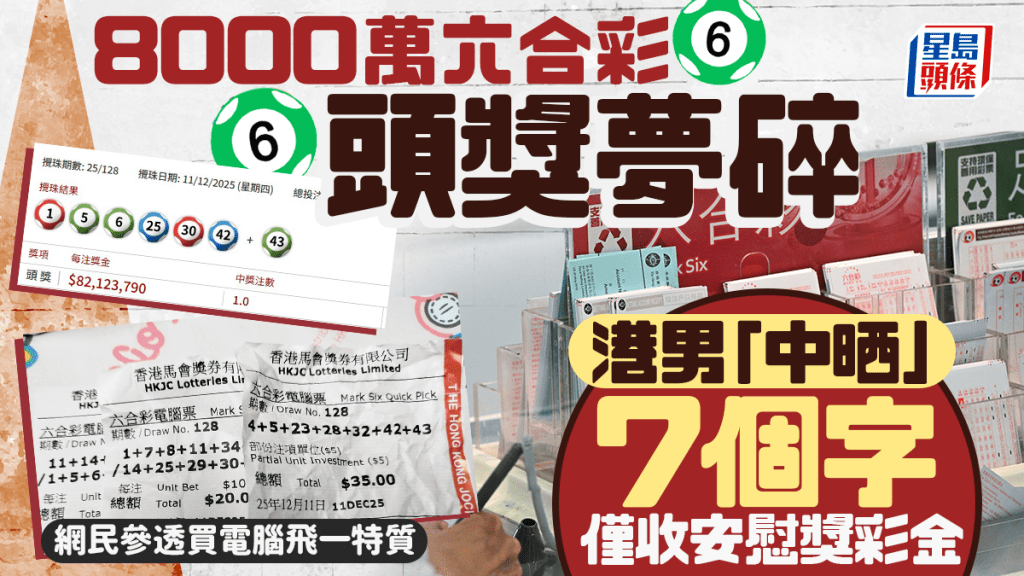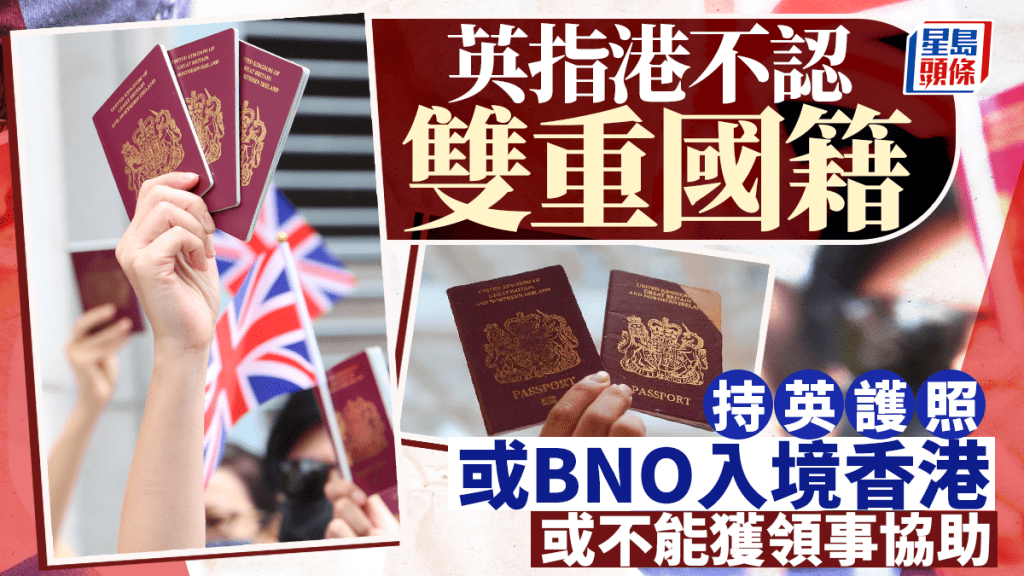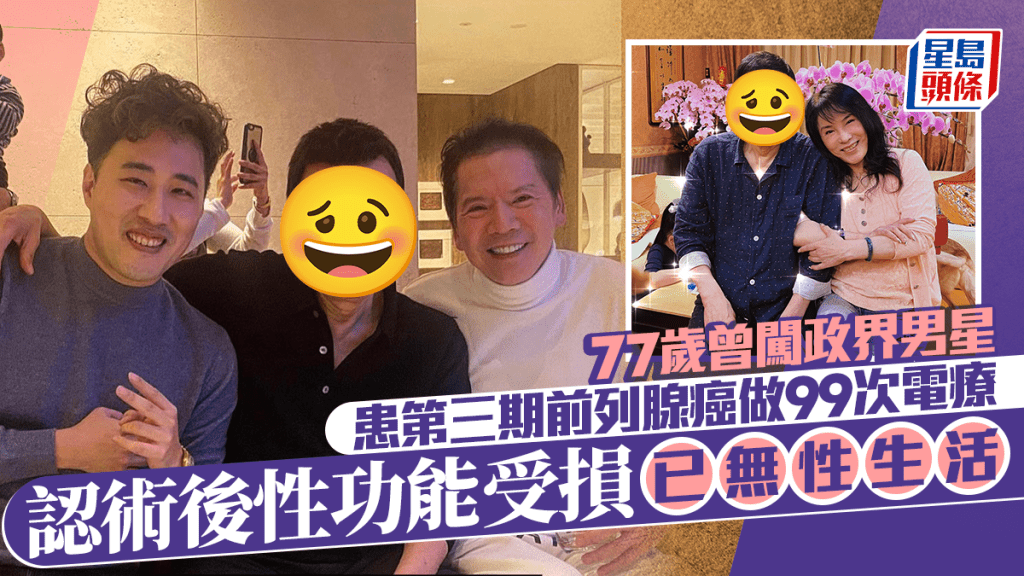雷射针——南京大屠杀的教育意义
二○一四年人大常委决议把每年的十二月十三日订为「国家公祭日」,以纪念在南京大屠杀中丧生的亡灵。
这个决议非常正确。在一九三七年的这一天,日本侵华部队在其华中军总司令,战后被国际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绞死的松井石根率领下,耀武扬威的操入南京城。这名总司令给予了日军一天假期,以便他们到处奸淫掳掠,以杀人为乐。但此等暴行又岂止是一天之事?在其后四十多天,共三十万无辜平民被杀,有人算过他们身上流的血液,几近一千五百吨,当中不少被推入位处今天「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位置的万人坑中,妇女婴儿也不被放过。但在十二月十三日同一天,东京却有百万人涌到街头庆祝,欢声震天。
这段灭绝人性的历史,日本不但从来没有仿效德国总理跪倒纪念遭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纪念碑前道歉,反而一众政要过时过节便去参拜供奉了松井石根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这是何等对生命不尊重的心态?有日本这样一个邻国,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我们能忘记历史,麻木不警惕乎?但偏偏在香港,却有对历史无知,胡涂透顶的某些家长,要投诉某中学播放的一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短片,不满当中的残忍镜头,又有人认为学校只是「为势所逼」才放这段电影。「为势所逼」一词暴露了这名家长的心态,他或她应是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知道「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如果香港有大部份的家长及教师抱有此等教育观,则香港的下一代有大概率会沉沦,不懂明辨是非,也无竞争力。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中的大事,当中可供学习的教材十分丰富,值得挖掘。若家长及教师有适当引导,孩子可培养出对生命的尊重,对凶残的反感,对和平的热爱。年纪较大的还可探索为何人类中有如此可怕的天性。见识过凶残及知道日本侵略军最终失败,也可使孩子更有勇气去面对可怕的敌人。在人生事业中,勇气是成功的一个必要因素。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现有所谓的「安全区」的概念,即学生有权不用见到他们不想见的事物,不用听到他们不想听的言论,此种把年轻人当作温室里花朵的做法,正在为美国培养出一批废物,香港岂能学习?
但在南京这段可怖的历史中,我们又可见到人性的光辉在闪耀。当时有一批在南京的洋人,他们是商人、传教士、教授、医生等等,都因为对日军的兽行看不下去,冒着极大的危险,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拯救并庇护了近二十万名南京市民。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德国西门子公司派在南京的员工拉贝(John Rabe),他牵头把金陵大学及美国领事馆作为核心区,在今天南京市新街口西北面三点八六平方公里的地区,成立了一个「南京安全区」,让难民保住性命。他有此能耐与日军讨价还价,部份原因是他自己竟是一名坚定的纳粹党!拉贝来华前后共三十年,在一九三四年因为要创办一间让德国侨民子弟读书的学校,向德国政府申请拨款,于是加入了纳粹党。在那段风雨飘摇,要保护并养活20万人的日子中,他被南京人民视为活菩萨,也成了世界名人,与他一起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美国人魏特琳(Minnie Vautrin,又名华群)也被视为圣母、观音菩萨。拉贝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被迫离开南京,4月回到德国,受到纳粹的重重盘问,战后,苏联红军倒是知道他的大名,善待他,但在战后废墟中,他也穷途潦倒,宋美龄向南京市民募捐,倒是送了一笔钱给他解困。这批建立「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友人除了让我们见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及人心的复杂外(纳粹党也可以有好人),也留下了大量历史原始材料让我们辨别事实的真伪。他们似乎有写日记的习惯,当中多名当事人都留下了日记,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有人拿着摄影机到处拍摄,使我们得见不少图片及纪录片。后来,亦有不少有心人访问过幸存者,记敍了他们的口述历史,再加上当时的国际媒体报道,各种资料互相印证,「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可谓铁证如山。在作出任何道德判断前有一步是不能免去的,便是搞清楚证据是否可信,不能人云亦云,这也是公民教育及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份。教师、家长及教育局,宜充份掌握这些材料,消化后因才施教,让学生怎么从材料的对比中找出结论。
说到材料,不能不提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及作家张纯如。她一九六八年出生,祖父母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自幼听祖父母描述当年经历。研究院毕业后,她插集了大量外籍人士对大屠杀的记录,特别是重新发现几乎已湮没了的近二千页的《拉贝日记》,出版了畅销五十余万本的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使世人重新记忆起这段历史。她在二○○四年因抑郁症吞枪自尽,虽说她是长期失眠及受药物后遗症影响,但我总怀疑她多多少少是在看到了这么多悲惨材料后,精神有点承受不了。所以学校搞相关教育,也要因应不同年龄小心取材。
搞「南京大屠杀」教育,目的不应是煽动仇恨,而是要我们对人性的卑劣产生戒心,并且明白争取和平的可贵与必要性。此点也应是教育的一部份。
雷鼎鸣
这个决议非常正确。在一九三七年的这一天,日本侵华部队在其华中军总司令,战后被国际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绞死的松井石根率领下,耀武扬威的操入南京城。这名总司令给予了日军一天假期,以便他们到处奸淫掳掠,以杀人为乐。但此等暴行又岂止是一天之事?在其后四十多天,共三十万无辜平民被杀,有人算过他们身上流的血液,几近一千五百吨,当中不少被推入位处今天「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位置的万人坑中,妇女婴儿也不被放过。但在十二月十三日同一天,东京却有百万人涌到街头庆祝,欢声震天。
这段灭绝人性的历史,日本不但从来没有仿效德国总理跪倒纪念遭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纪念碑前道歉,反而一众政要过时过节便去参拜供奉了松井石根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这是何等对生命不尊重的心态?有日本这样一个邻国,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我们能忘记历史,麻木不警惕乎?但偏偏在香港,却有对历史无知,胡涂透顶的某些家长,要投诉某中学播放的一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短片,不满当中的残忍镜头,又有人认为学校只是「为势所逼」才放这段电影。「为势所逼」一词暴露了这名家长的心态,他或她应是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知道「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如果香港有大部份的家长及教师抱有此等教育观,则香港的下一代有大概率会沉沦,不懂明辨是非,也无竞争力。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中的大事,当中可供学习的教材十分丰富,值得挖掘。若家长及教师有适当引导,孩子可培养出对生命的尊重,对凶残的反感,对和平的热爱。年纪较大的还可探索为何人类中有如此可怕的天性。见识过凶残及知道日本侵略军最终失败,也可使孩子更有勇气去面对可怕的敌人。在人生事业中,勇气是成功的一个必要因素。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现有所谓的「安全区」的概念,即学生有权不用见到他们不想见的事物,不用听到他们不想听的言论,此种把年轻人当作温室里花朵的做法,正在为美国培养出一批废物,香港岂能学习?
但在南京这段可怖的历史中,我们又可见到人性的光辉在闪耀。当时有一批在南京的洋人,他们是商人、传教士、教授、医生等等,都因为对日军的兽行看不下去,冒着极大的危险,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拯救并庇护了近二十万名南京市民。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德国西门子公司派在南京的员工拉贝(John Rabe),他牵头把金陵大学及美国领事馆作为核心区,在今天南京市新街口西北面三点八六平方公里的地区,成立了一个「南京安全区」,让难民保住性命。他有此能耐与日军讨价还价,部份原因是他自己竟是一名坚定的纳粹党!拉贝来华前后共三十年,在一九三四年因为要创办一间让德国侨民子弟读书的学校,向德国政府申请拨款,于是加入了纳粹党。在那段风雨飘摇,要保护并养活20万人的日子中,他被南京人民视为活菩萨,也成了世界名人,与他一起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美国人魏特琳(Minnie Vautrin,又名华群)也被视为圣母、观音菩萨。拉贝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被迫离开南京,4月回到德国,受到纳粹的重重盘问,战后,苏联红军倒是知道他的大名,善待他,但在战后废墟中,他也穷途潦倒,宋美龄向南京市民募捐,倒是送了一笔钱给他解困。这批建立「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友人除了让我们见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及人心的复杂外(纳粹党也可以有好人),也留下了大量历史原始材料让我们辨别事实的真伪。他们似乎有写日记的习惯,当中多名当事人都留下了日记,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有人拿着摄影机到处拍摄,使我们得见不少图片及纪录片。后来,亦有不少有心人访问过幸存者,记敍了他们的口述历史,再加上当时的国际媒体报道,各种资料互相印证,「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可谓铁证如山。在作出任何道德判断前有一步是不能免去的,便是搞清楚证据是否可信,不能人云亦云,这也是公民教育及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份。教师、家长及教育局,宜充份掌握这些材料,消化后因才施教,让学生怎么从材料的对比中找出结论。
说到材料,不能不提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及作家张纯如。她一九六八年出生,祖父母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自幼听祖父母描述当年经历。研究院毕业后,她插集了大量外籍人士对大屠杀的记录,特别是重新发现几乎已湮没了的近二千页的《拉贝日记》,出版了畅销五十余万本的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使世人重新记忆起这段历史。她在二○○四年因抑郁症吞枪自尽,虽说她是长期失眠及受药物后遗症影响,但我总怀疑她多多少少是在看到了这么多悲惨材料后,精神有点承受不了。所以学校搞相关教育,也要因应不同年龄小心取材。
搞「南京大屠杀」教育,目的不应是煽动仇恨,而是要我们对人性的卑劣产生戒心,并且明白争取和平的可贵与必要性。此点也应是教育的一部份。
雷鼎鸣
最Hit
长者乘车优惠明年4月收紧!长者群组热议「两蚊两折」点样计? 每月限搭240程?北上深圳贵好多?
2025-12-12 17:51 HKT
长寿秘诀|90岁烘焙师仍出书主持节目 公开3大饮食习惯 保持健康绝不吃1类食物
2025-12-13 10:14 HKT
奇闻秘史︱同治皇帝传染花柳驾崩 慈禧当日点处治「嫖娼指南」王庆祺?
2025-12-13 07:00 HKT
港人重返职场做满1年额外「收政府$2万支票」 附2大中年再就业/求职津贴申请方法
2025-12-12 17:26 H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