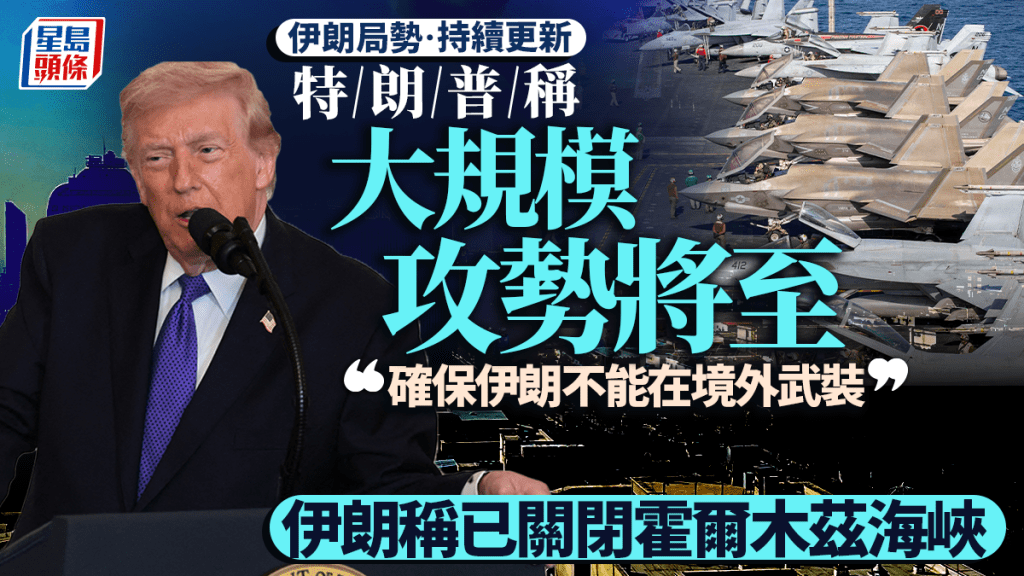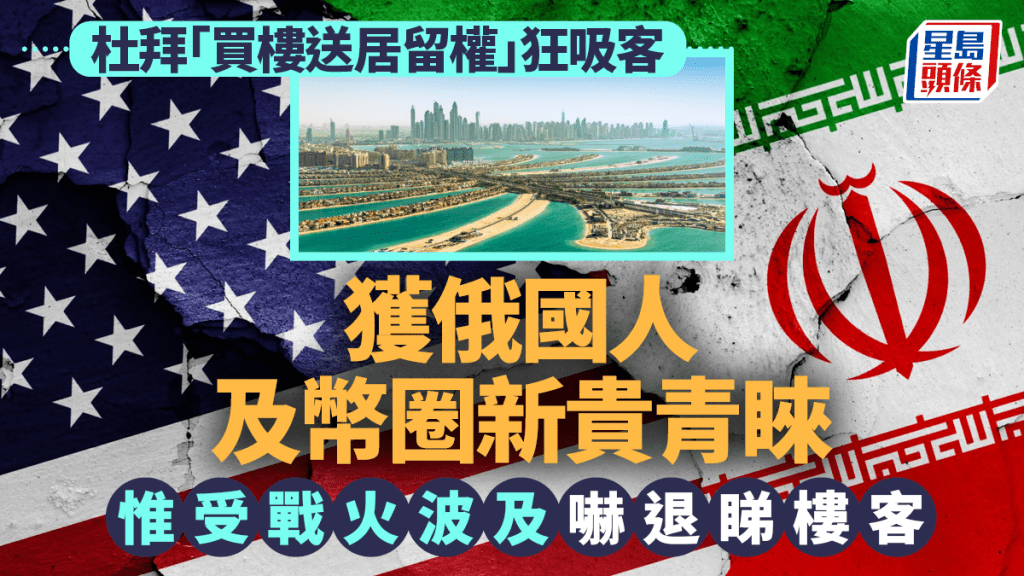每日杂志‧人物志|走进战区从死神手中抢救生命 吴少彬盼更多医者投入人道救援
发布时间:08:00 2025-12-04 HKT

「未来会发生甚么事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伤者可能之后会死亡,又或许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香港红十字会医护人员、麻醉科医生吴少彬(Ben)今年3月远赴加沙,展开为期6周的人道救援工作。在战火不断的环境中,他日以继夜抢救大量伤者,目睹年幼孩童被炸弹重创,成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说,未来会继续前往不同战地,盼尽己所能拯救更多生命,也期望未来有更多年轻医生投身人道救援的行列。日前,大埔宏福苑火灾中,他亦再次投入前线,运用战地救援的经验,帮助灾民。
Ben早于2006年起参与国际人道救援工作,曾前往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及南苏丹等地。今年3月,他远赴加沙,展开为期6周的救援任务,「我喜欢去一些越紧急、越少人去的地方。」

初到当地正值短暂停火,比想像中安静,他一度以为情况或许稍为稳定。然而平静只是幻象,停火协议破裂后,爆炸声连绵不绝,大批炸伤及断肢的病人被送入医院,团队没有时间休息,不停地与死神搏斗。
医院内部早已因应战况加固,手术室帐篷除了门口外,三面均堆满沙包防弹,更设置货柜箱改建而成的「安全屋」,以备武装分子突入扫射时能立即躲避。他说,经常听得见外面的枪声、爆炸声,只能加快速度、保持冷静地完成眼前的手术,「因为走出去的风险更大,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难忘女孩被铁片割开脸断手指
战争中伤亡惨重的,往往是「跑得慢」的妇孺。他难忘曾有一名10多岁的女孩,被炸飞的铁片割开脸部。尽管他与团队为女孩紧急缝合,然而其部分手指已被炸断,「这些伤痛不应该由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去承受,就算我们救了她一命,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如何生存下去?」

大量伤者涌入,令本已匮乏的医疗资源变得更捉襟见肘。Ben说,有时血库只有10包血,如何分配成为最艰难的抉择,「伤势极重、流血不止者,可能一个人就要输10包血才勉强救回;但同样的血量,或许能救到5名只需1至2包血的伤者,你选择救谁?」
他坦言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下,不是所有人都能救回;当知道伤者即使救回,也可能无法在当地医疗系统存活时,只能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我们会将他转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按照合适的宗教仪式,让他可以有尊严地与家人告别,接着为他注射大量的吗啡,使其在相对不痛苦的情况下离世。」
他感慨,生命无比珍贵,但在资源短缺的战地,无奈要作出取舍,「每个人都能救当然是最好,但是现实很多时候做不到。」

除了伤者,Ben还要面对医护同袍的离世。由于不少伤者无法自行前往医院,需要出动救护车深入地区支援,「曾有司机和医疗团队遭遇枪击死亡,他们都是巴勒斯坦当地的人员。」
虽然住所与医院只相隔10多米,却是最紧张的一段路。每次出门,Ben都要等待医院与住所的门卫对接,「看到对面开门后,门卫会告诉我可以过去了,我就用最短的时间横跨10几米走到对面。」短短几步路,在战区中却可能攸关生死。
由于加沙安全系数极低,团队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医院与住所的「两点一线」,他形容就像住在一座大一点的「监狱」,「任何时间都有机关枪声,看见无人机在半空盘旋。」他指,当地严禁人员上屋顶,因为以色列军队若看到有人在屋顶,就会怀疑是恐怖分子,进而射杀,因此人道救援最多只能留6周,否则有机会影响精神健康。
强大心理与幽默感挨过「监狱」生活
如何调节心态,Ben称强大的心理与幽默感是关键,努力在恶劣的环境中,抓住生活中微小的美好,「加沙的日出日落很美,雨后还有彩虹。」在医院巡房时,他常见到病人把仅余的食物喂给猫,难得的温馨冲淡了些许战争的沉重。他亦喜欢逗弄小朋友,看到他们的笑容,便觉得开心。空闲时,他也会冥想,沉淀心绪,提醒自己要照顾身体,「如果吃不好、睡不好,又怎么在那个环境下做事?」


他表示,麻醉科医生不如外科医生受外界关注,通常在手术台的布帘后工作,却是决定病人生死的关键,「由我们决定输多少血,手术结束后也是靠麻醉科医生观察病人的呼吸、血氧,及进行术后止痛等工作,责任和重要性不比外科医生低。」
回顾多年的人道救援工作,Ben说自己也在过程中蜕变成更冷静的人,「每一次的救援都是经验的累积,最珍贵的是记忆,无论是对那里的人,还是地方。」

「如果纯粹用钱的角度看,我们是一群傻瓜。」他想帮正在受苦的人减轻一点痛楚。他叹道,看过太多妇孺被卷入战争中,没有避难能力,也没有逃生速度,「战争的受害者永远是弱势那批。」
本身已有急症科专科资格的Ben,为了在战场上能救回更多生命,多年来不断进修,包括获麻醉专科资格,「能力越大,可以做的事就越多。」他提到,由于落后地区经常断电,全身麻醉的要求及风险亦相对较高,而区域性麻醉只需将药物经针筒注射到目标身体部位,便能麻痹神经,在资源有限的地方派上用场。


他指,参与人道救援的麻醉科医生数量不多,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医生投身行列,将专业知识带到有需要的地方。他提醒,参与人道救援不应只学技术,也要理解战争背后的文化与历史,否则永远看不到事件全貌。
五级火灾翌日随中大团队支援
回到香港,Ben的救援工作并未停下。大埔宏福苑上周发生五级大火,他翌日便随中大医院团队前往东昌街社区会堂支援。当时大火仍未完全救熄,现场欠缺中央指挥,情况相当混乱。
然而,曾在战地处理紧急救援的Ben,对那种混乱反而相较熟悉。他回忆,医护团队与药剂师学会临时建立合作,迅速找来电脑并成功登入「医健通」,为无法回家取药的长期病患者诊症及处方药物;一些突发头晕、呕吐或腹痛的病人,则作基本检查,按需要提供药物;遇上血糖过高的糖尿病长者,只能立即召救护车送院。
对于未来打算,Ben坚定地说,会继续人道救援工作,有合适的地方就会争取,「最主要看当时需不需要、适不适合,如果没有人去医治,我就去。」

从急症科到麻醉科 深信能力越大可做更多
Ben形容,走上人道救援这条路,并非一开始就有明确方向,日本留学的经历让他发现人生的新方向。
他忆述,早年曾获奖学金到日本交流1年,修读日本现代史,过程中接触不同国籍的老师,「教日本史的是一位美国人,教授日本传统音乐的则是一位澳洲人」,发现原来外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居然能比当地人深入,「那时候就埋下一颗种子,我将来也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或者别人觉得特别的事。」
于是,他在2006年首次参与无国界医生的人道救援。然而,真正踏入战地救援后,他才意识到急症科的专业,仍不足以支撑复杂的战地手术。当他遇见因地雷炸断手脚,却无法接受适当手术的伤者,内心深受震撼,「如果自己能做更多就好了。」这念头最后推动他在人生已进入30岁时,毅然选择进修麻醉科。
重新回到训练的位置并不容易。Ben说,当时难免遇到异样的目光,有人会质疑他不了解麻醉,也有人会因其专科医生的身份而不好意思教导,「情商要很高才能游走在两边。」但他说,过程中也学会了谦卑,「越是觉得别人厉害,就越应该去学,学完就是你的能力。」
辞公院工作 自由身「接单」
从急症科到麻醉科,他用了6年重新训练,由于希望累积更多临床经验,他考获麻醉科专科后继续在医院工作。他认为,人道救援需要极高的技术,因此必须比本地毕业标准再高一点,才能在资源匮乏的环境维持医疗质素,「有些地区只有一名麻醉科医生。如果你搞不定,不能喊救命。」
待储备足够知识及信心,他才重返国际救援前线,先后前往南苏丹、加沙等地参与救援,「是时候补回中间10多年的空白。」为了每年都能抽出2个月时间参与人道救援,他最终辞去公立医院的工作,成为自由身麻醉科医生,并兼职急症科。
访问期间,Ben不时就会看手机,回复讯息。他笑言如今的工作模式像「网约车」接单,有时靠相熟的医生介绍工作,却不用再受限于任何团体。
记者:潘明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