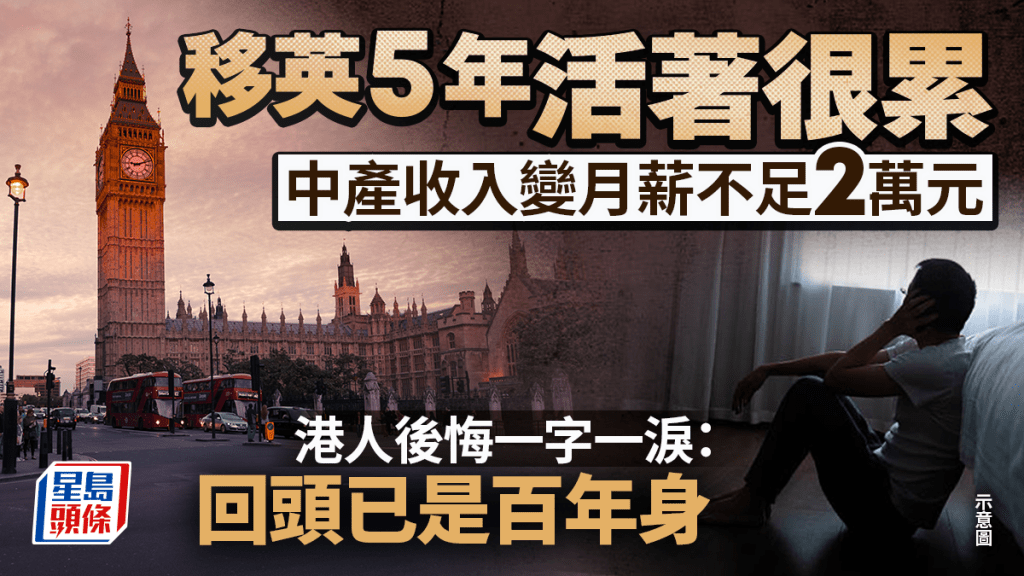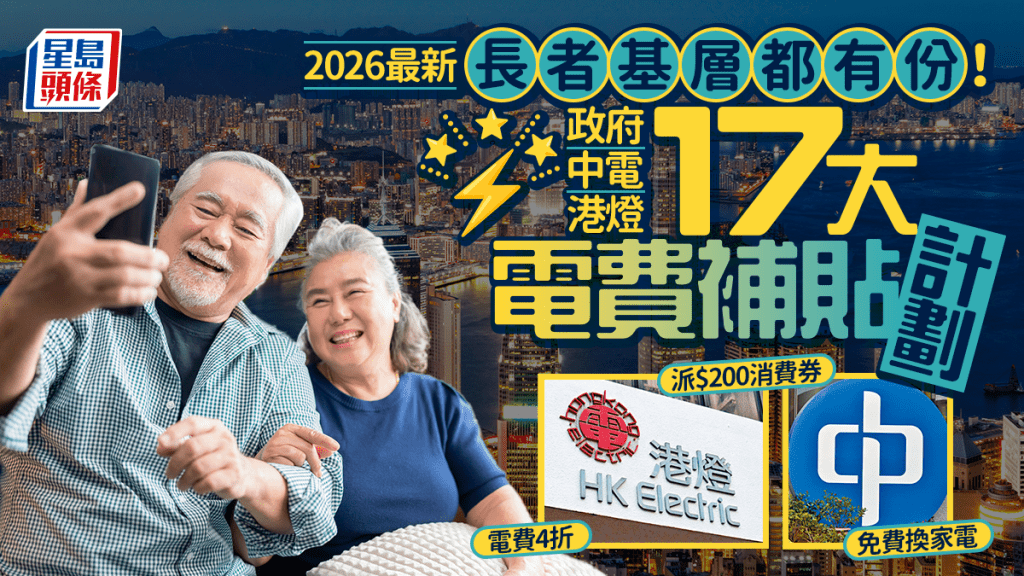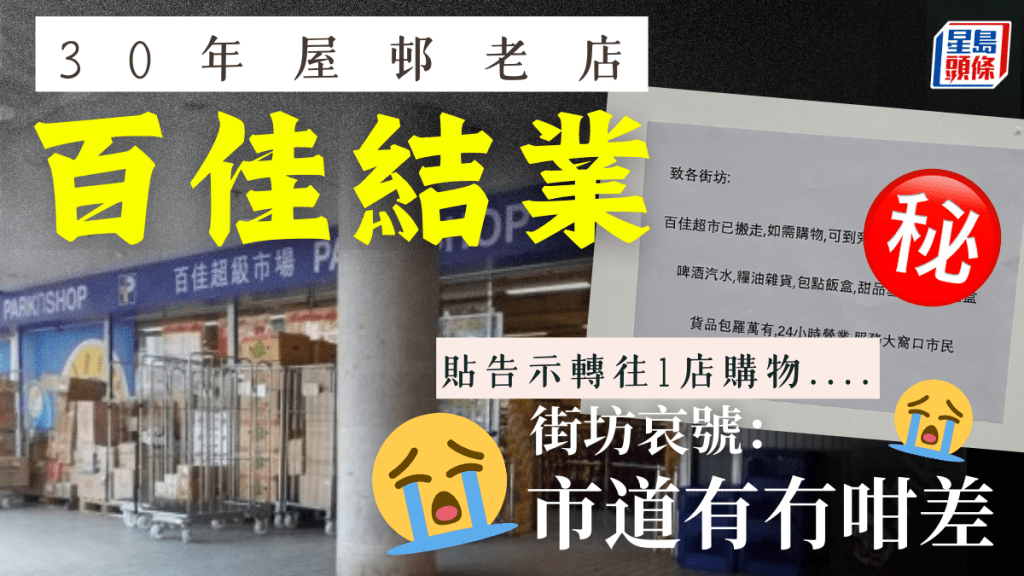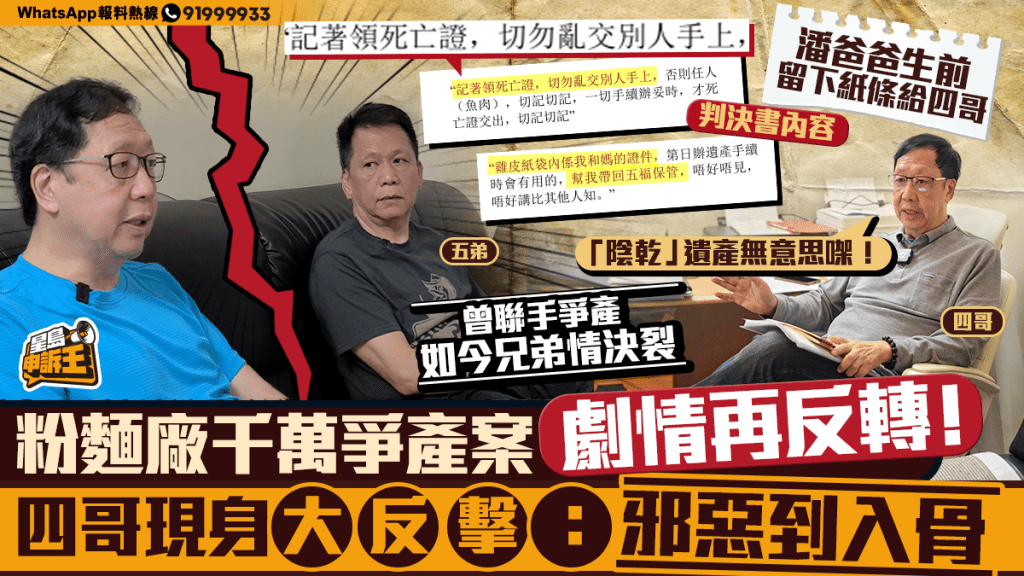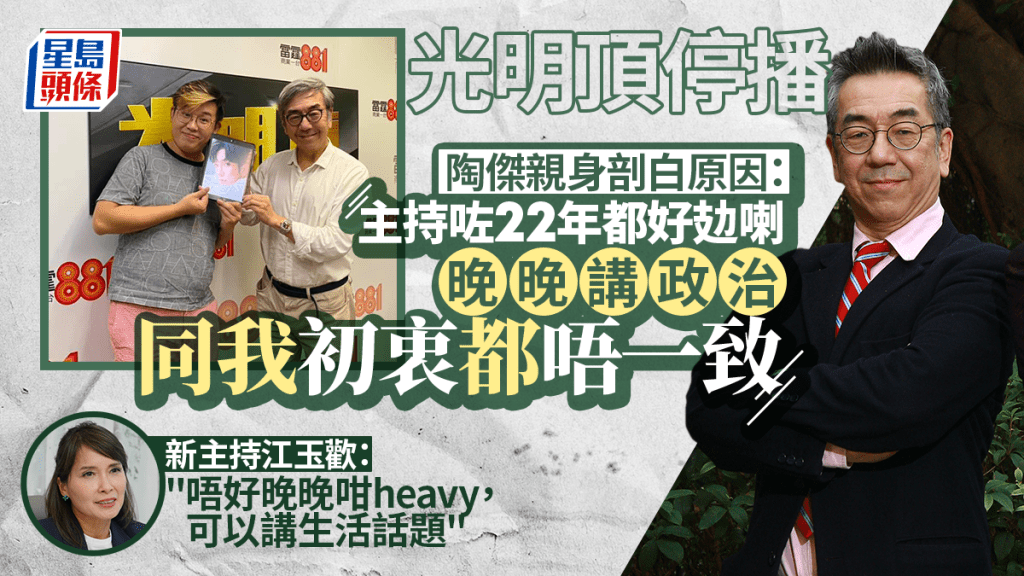辛正儿 - 改革医务委员会 打破「医医相卫」 | 社论

一宗医委会聆讯竟拖延15年,正义感在时间流逝中消磨殆尽。一名双非婴儿脑瘫案件,家属苦等15年,换来的却是医委会以「拖延太久对被告不公」为由永久搁置聆讯,父亲悲愤道:「现在香港好像连第三世界都不如!」对香港医疗投诉机制,作出沉重的控诉。
医委会作为法定监管机构,其「医医相卫」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当前的危机不仅是个别案件处理失当,更是整个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医委会组成存在先天缺陷,根据《医生注册条例》,医委会由24名医生和8名业外委员组成,医生委员占总数的75%,这种绝对多数,令人觉得,业外意见难以影响决策。
尽管2018年改革增加了业外委员比例,但医生群体在专业自主的大旗下,仍牢牢掌握着主导权。这种封闭的权力结构,难免给公众造成「医医相卫」的负面印象。在专业权威光环下,医生的专业判断往往成为不容挑战的「真理」。医疗事故的调查过程复杂专业,一般公众难以置评,这种信息不对称强化了医生的话语权。在这种不平衡权力结构下,投诉人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他们不仅要面对专业知识的壁垒,还要挑战一个由同行组成的封闭圈子。
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效率低下,已成制度性问题。根据数据,过去5年医委会合共跟进了8700宗申诉,当中8成被驳回,只有不足3%个案需要开纪律聆讯。而平均研讯时间长达6年,当中有7宗需要7至8年处理,更有3宗耗时超过10年。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苦苦等待公义的家庭。
程序拖延不仅消耗投诉人的时间金钱,更是对他们精神的残酷折磨。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医委会研讯小组在双非子脑瘫案中,以「案件拖延太久对被告不公」为由决定终止聆讯。这意味着医委会自身的失误,最终成了被投诉医生免于追究责任的理由。如此决策逻辑,完全颠覆了公众对正义的认知。
2018年的改革未触动医委会权力结构的核心,只是边际上的调整。要打破「医医相卫」的困局,必须从制度结构入手。首先应大幅增加医委会中业外委员的比例,借鉴英国经验将非医疗委员的比例提高至百分之40。这不仅是数量的调整,更是权力结构的重整,让业外意见真正具有影响力。
其次,设立独立的医疗事故投诉处理机制。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鸿昌建议,医委会应参考死因庭的案件管理程序,目标在两年内完成聆讯。而本港亦应参考英国建立全国医疗安全调查办公室的经验,成立独立于医委会的投诉处理机构,彻底改变现行医生自己审判自己的局面。
程序改革方面,必须引入合理的时限要求和案件管理制度,并定期向投诉人通报进展。同时增加调查过程的透明度,让公众能够监督医委会的运作。
辛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