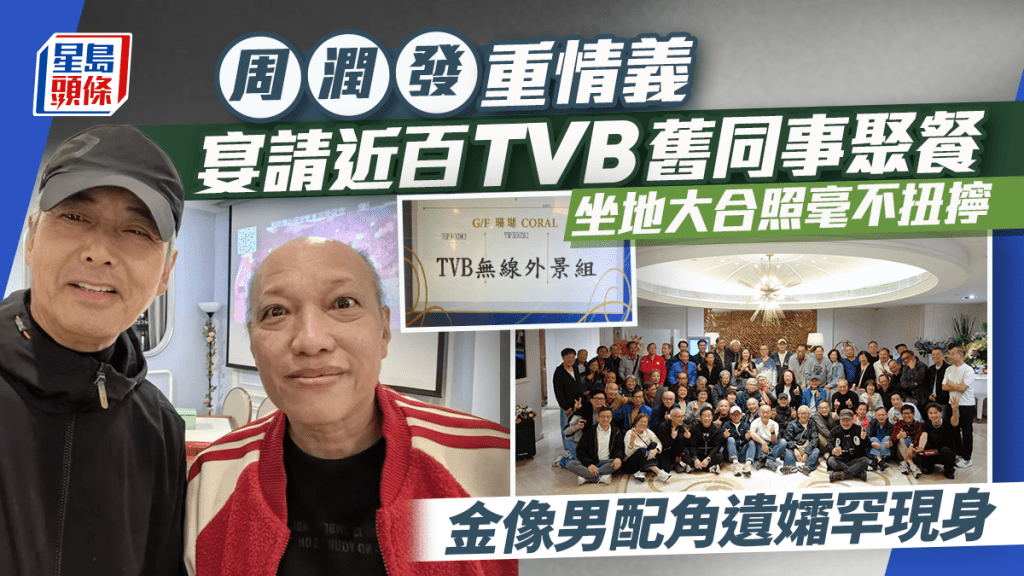巴士的点评——等找到民主共识后,人都死了
香港政府计划动用《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对有轻微病征的病人进行强制检测。今早听电台清谈节目,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话与政府官员开会,谈到这个问题。蔡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虑,说市民对政府信任度低,事情很难进行,若要求轻微病征患者做检测,成效不大,又担心会破坏医患关系。总而言之,他对强制轻症病人检测有保留。
一个病人权益组织的人士接受访问时又认为,强制检测破坏了医生保障病人私隐的互信,担心会令市民不敢求医。他认为不应强制,应该教育有病征的病人去检测。在你一言、我一语之下,政府想要求有病征的病人强制检测,在上述讨论中又变成一件错漏百出的事情,没有共识,不应进行。
整件事发生的缘起是咁的。内地一有疫症爆发的地区,就会马上进行大规模检测,发现一个确诊者,会检测相关大范围的一万人。如果出现十个八个确诊者的小型爆发,就会整个城市进行强制检测,找出所有潜在的传播者。这个做法在北京、乌鲁木齐和青岛都试行过,卓有成效,快速清零。见到内地控疫成功,不少人建议特区政府进行全民强制检测。
但香港有部份医生不知道是基于政治偏见抑或专业偏执,对内地的抗疫做法相当抗拒,他们认为全民强制检测「无效率」。而特区政府害怕这样做会有很多市民反对,认为干涉到个人自由,所以一直不敢作出决定。随后政府做了一些「中间落墨」的方法,例如自愿性的全民检测、在疫情较严重的地区开设自愿检测中心等等。到最近部署修改法例,对有轻微病征的病人进行强制性检测。其实,这个建议也是由专家们提出的。
例如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早前就提议,私家医生可以强制检测有病征者。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就话,大部份家庭医生,如发现病人有任何病征,如上呼吸道感染或有肠胃炎,他们都会呼吁病人进行检测,但只有约一半人会听从,但经私家医生找到确诊者的命中率颇高,每百名接受检测的病人,便会有一至二人最终确诊。他认为最好强制有病征市民进行检测,但在现时社会环境下相信很难实行。
政府听从了专家的建议,便计划修例要轻症病人进行强制检测。政府这个建议一出,又涌出另一批人说这样做会损害这样、影响那样。
整件事有点荒谬可笑,就好像一个怪圈在无限旋转,转来转去,政府甚么意见都听取,结局就甚么也做不到。因为每个问题的都有十种意见,而反对声音总是比较响亮,最后政府就是不做不错。
从效率而言,只强制检测轻症病人,的确有缺憾,因为这只有从检测过程获取确诊者的效率,却没有全民强制检测的可以尽快清零的社会整体效率。当社会因为限聚令而每天损失七亿元时,能够快速清零的方法,才是整体上最有效率的方法。
政府不敢做最佳的选项(全民强制检测),唯有采用次佳选项(强制轻症者检测)。这个做法虽然对清零的作用较低,但起码可以找出更多的带病毒者,但依然遭到反对。可见在政治挂帅的社会,甚么事情也做不成。
这让我想起名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佛里曼所讲的:「美国没有一个威权政府,我们也不希望有一个。但我们未能产生一个民主共识,来进行同样的(抗疫)工作。」如果香港在抗疫上要学习美国,很容易会得出美国的结果。美国人口三点三亿,香港七百五十万,以美国单日确诊人数五点七万人推算,香港单日确诊就会是一千二百九十五人;美国累计有八百四十六万人确诊,香港就会有十九点二万人确诊。这就是美国寻求民主共识(可能永远寻找不到)的人命代价。等找到民主共识后,人都死了。
抗疫是行军打仗,讲求高度效率。香港这种吵吵闹闹的方式,情况虽然好过外国,但远差过内地,经济就会差下去。十一月过后,政府的保就业计划结束,全社会都要挨大裁员大减薪的冲击,残忍一点说,拖延行动,自食其果,与人无尤。
「巴士的报」是一份网上报纸,让网民随时随地拿着手机或平板电脑可以看到。www.bastillepost.com
[email protected]
卢永雄
一个病人权益组织的人士接受访问时又认为,强制检测破坏了医生保障病人私隐的互信,担心会令市民不敢求医。他认为不应强制,应该教育有病征的病人去检测。在你一言、我一语之下,政府想要求有病征的病人强制检测,在上述讨论中又变成一件错漏百出的事情,没有共识,不应进行。
整件事发生的缘起是咁的。内地一有疫症爆发的地区,就会马上进行大规模检测,发现一个确诊者,会检测相关大范围的一万人。如果出现十个八个确诊者的小型爆发,就会整个城市进行强制检测,找出所有潜在的传播者。这个做法在北京、乌鲁木齐和青岛都试行过,卓有成效,快速清零。见到内地控疫成功,不少人建议特区政府进行全民强制检测。
但香港有部份医生不知道是基于政治偏见抑或专业偏执,对内地的抗疫做法相当抗拒,他们认为全民强制检测「无效率」。而特区政府害怕这样做会有很多市民反对,认为干涉到个人自由,所以一直不敢作出决定。随后政府做了一些「中间落墨」的方法,例如自愿性的全民检测、在疫情较严重的地区开设自愿检测中心等等。到最近部署修改法例,对有轻微病征的病人进行强制性检测。其实,这个建议也是由专家们提出的。
例如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早前就提议,私家医生可以强制检测有病征者。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就话,大部份家庭医生,如发现病人有任何病征,如上呼吸道感染或有肠胃炎,他们都会呼吁病人进行检测,但只有约一半人会听从,但经私家医生找到确诊者的命中率颇高,每百名接受检测的病人,便会有一至二人最终确诊。他认为最好强制有病征市民进行检测,但在现时社会环境下相信很难实行。
政府听从了专家的建议,便计划修例要轻症病人进行强制检测。政府这个建议一出,又涌出另一批人说这样做会损害这样、影响那样。
整件事有点荒谬可笑,就好像一个怪圈在无限旋转,转来转去,政府甚么意见都听取,结局就甚么也做不到。因为每个问题的都有十种意见,而反对声音总是比较响亮,最后政府就是不做不错。
从效率而言,只强制检测轻症病人,的确有缺憾,因为这只有从检测过程获取确诊者的效率,却没有全民强制检测的可以尽快清零的社会整体效率。当社会因为限聚令而每天损失七亿元时,能够快速清零的方法,才是整体上最有效率的方法。
政府不敢做最佳的选项(全民强制检测),唯有采用次佳选项(强制轻症者检测)。这个做法虽然对清零的作用较低,但起码可以找出更多的带病毒者,但依然遭到反对。可见在政治挂帅的社会,甚么事情也做不成。
这让我想起名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佛里曼所讲的:「美国没有一个威权政府,我们也不希望有一个。但我们未能产生一个民主共识,来进行同样的(抗疫)工作。」如果香港在抗疫上要学习美国,很容易会得出美国的结果。美国人口三点三亿,香港七百五十万,以美国单日确诊人数五点七万人推算,香港单日确诊就会是一千二百九十五人;美国累计有八百四十六万人确诊,香港就会有十九点二万人确诊。这就是美国寻求民主共识(可能永远寻找不到)的人命代价。等找到民主共识后,人都死了。
抗疫是行军打仗,讲求高度效率。香港这种吵吵闹闹的方式,情况虽然好过外国,但远差过内地,经济就会差下去。十一月过后,政府的保就业计划结束,全社会都要挨大裁员大减薪的冲击,残忍一点说,拖延行动,自食其果,与人无尤。
「巴士的报」是一份网上报纸,让网民随时随地拿着手机或平板电脑可以看到。www.bastillepost.com
[email protected]
卢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