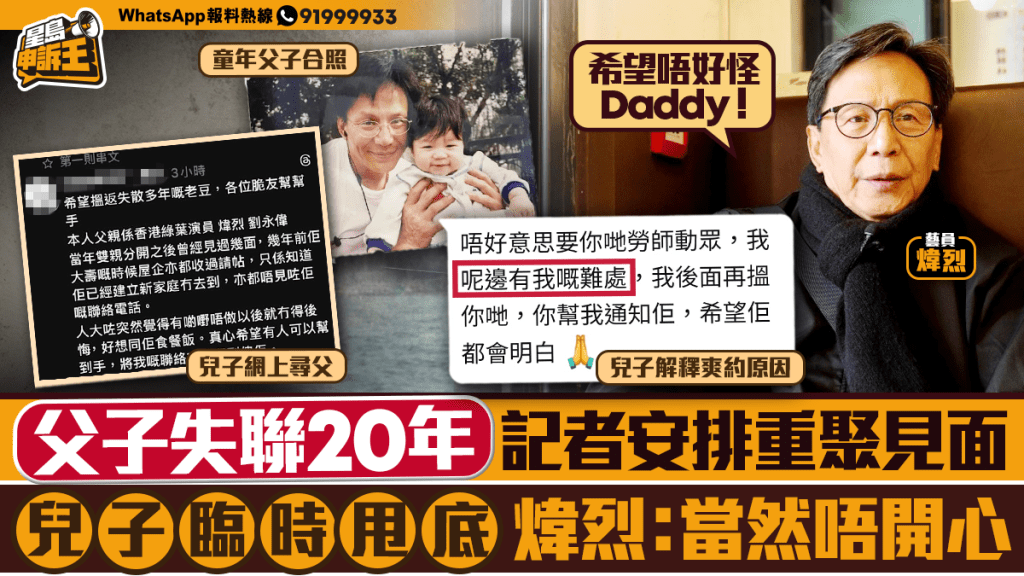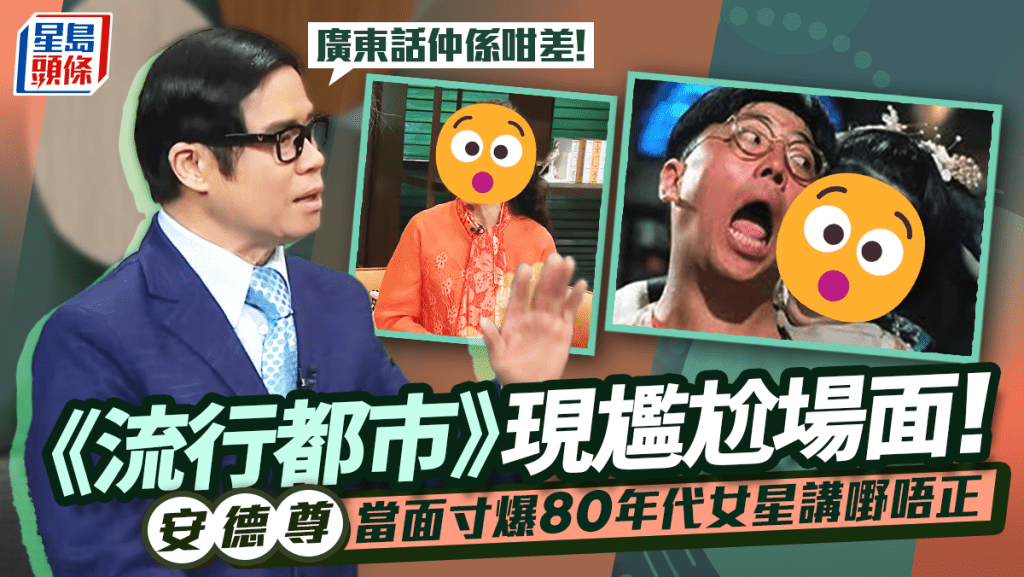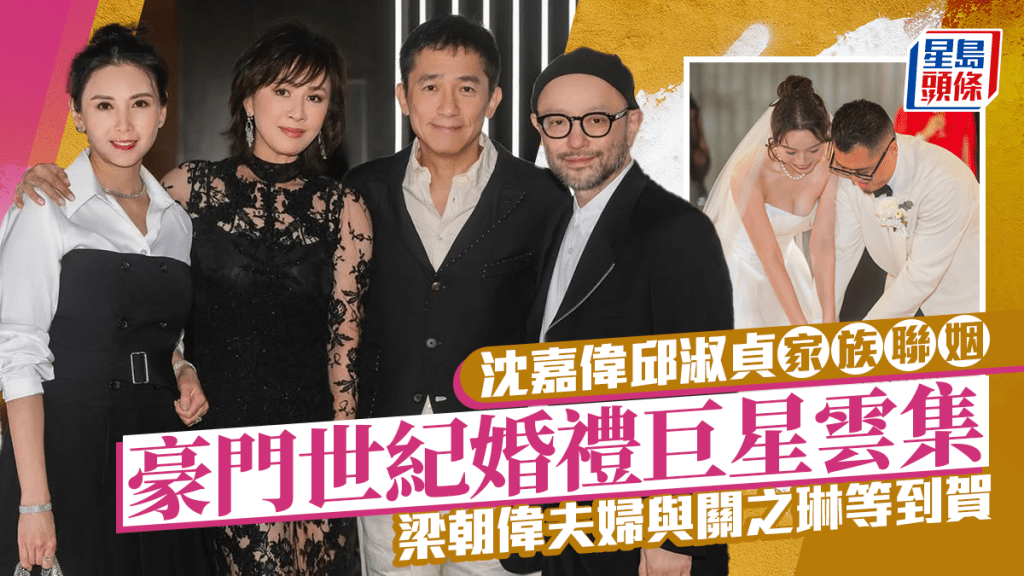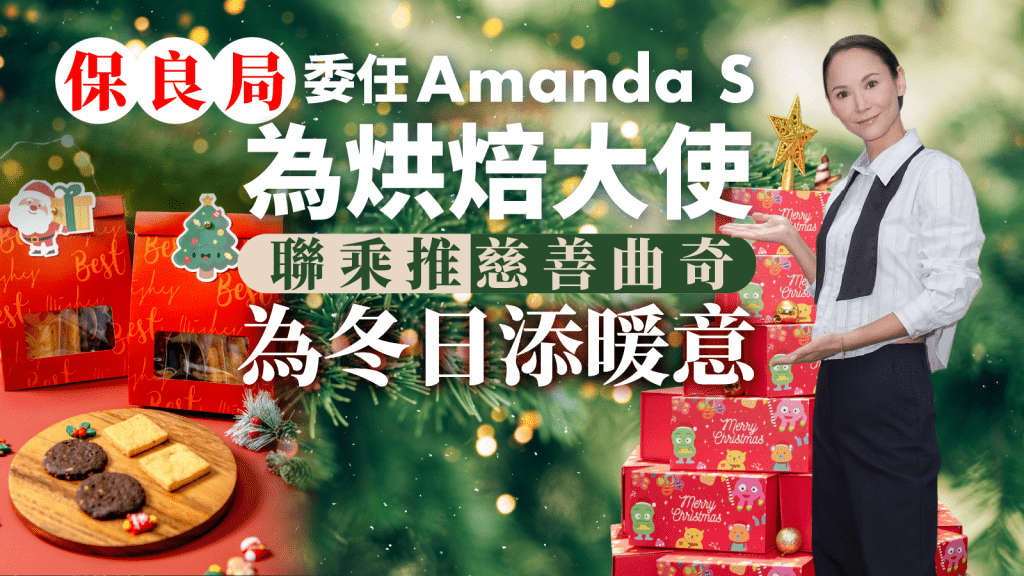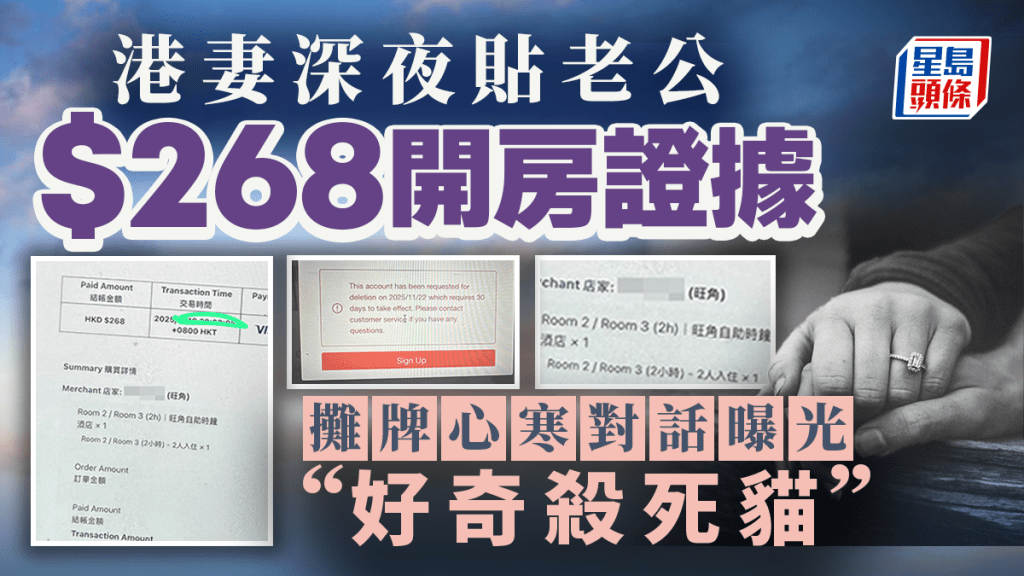10年漂泊「中途站」 矢志勇对未来鼓励同路人 免遣返声请者:何处是吾家
发布时间:03:00 2025-11-24 HKT

何处是「家」,是难民终身的疑问。Uzma Naveed生于巴基斯坦,由于其信奉的教派被视为「异端」,她自出生已活在阴霾之下,亲历家人及无数教友被逼害致死。10年前,她和家人来港寻求庇护,惟两度遭拒,面临被遣返之际,终在义务律师协助下,确立为无国籍的免遣返声请者。转眼间,她和家人在㓥房熬过疫情,儿子更已升上高中,但美加两地先后收紧难民政策,再次为其家庭带来不确定性。回首过去,她没想到自己有如此强大的韧性,面对将来,她勇于与家人携手面对,并分享其生命故事,鼓励同路人保持信念,终会迎来彩虹。
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而伊斯兰教有多个教派,当中Uzma家族信奉的「阿赫迈底亚」(Ahmadiyya)被视为「异端」,信徒屡受逼害,可随时被判入狱或处死,「我的父亲因为祷告而被捕,叔叔亦已受害。」Uzma坦言,无处可逃,亦无法隐瞒,因为所有身份证明文件也有标明宗教。
撇开信仰,Uzma的丈夫是纺织设计师,亦是一名橡胶滚筒厂商,她则在家相夫教子,二人皆拥大学学历。然而,他们自出生已活在阴霾之下,害怕成为下一个被逼害的目标,「每天也要看新闻,确保家人仍然在世;每当半夜收到电话,便生怕有意外发生。」她坦言,当生命受到威胁,必须取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难民,这不是我能选择的。」
10年前一家3口抵港寻庇护
10年前,Uzma与丈夫携同5岁的儿子离开,从巴基斯坦飞抵中国,再经陆路来港寻求庇护。她直言,此前从未听闻「香港」此地,「我们从来没有计划过,只知道香港会『安全』。」
然而,现行香港法律并不承认「难民」身份,港府自2014年实施「统一审核机制」,由官方统一审核免遣返声请,暂缓声称被遣返至其国家后会面对酷刑、权利受损或逼害等风险的申请者回到有关国家。自机制实行后,联合国难民处停止审核香港寻求庇护声请,改为由香港入境事务处审核;当声请者获港府确立及批出免遣返声请者资格,才可到难民处声请「难民」身份,再由署方为其进行第三国转移等计划。
靠津贴过活 住㓥房节衣缩食
对Uzma一家而言,自离开家园,人生已按下暂停键。花掉大部分积蓄来港,但等待免遣返身份需时,她和丈夫没有权利在港工作,只能依靠政府每月提供标准食物津贴以支撑生活,「平均每人每日有40元解决3餐。」至于租金,3人合共每月有3750元,仅足够于土瓜湾租住㓥房,「除了定期到入境处报到,我们基本上足不出户。」
等候获批出免遣返声请者资格的时间越长,Uzma越感不安。她说,每次报到都害怕被拘留,甚或即时被遣返至巴基斯坦,儿子亦要不断向学校请假。
随后8年,Uzma两度申请被拒,终在志愿律师协助下,上诉至高等法院才获胜诉,确立为无国籍的免遣返声请者。她忆述,首次被驳回的理由片面,「对方相信我们的宗教群体受逼害,但我们身上没有伤痕,更无枪伤。」
时光飞逝,Uzma难忘飞机起飞一刻,宛如踏上看不见终点的旅程,坐在身旁的丈夫更眼泛泪光;抵港后,一家滞留罗湖口岸,苦等14小时才获放行,职员递上一张地图,吁他们到重庆大厦求助。他们拿着两大袋行李,茫然地乘搭港铁,却不知何处下车,「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帮忙,感觉大家也很忙,看到我戴着头巾、说英文,更加抗拒。」
辗转到达重庆大厦,他们在商户介绍下,来到基督教励行会难民服务中心叩门,应门的社工Jeffrey成为Uzma一家的引路明灯,为他们提供人道援助、医疗和心理支援服务。她又说,疫情是最艰难的时间,迟迟未获安排注射疫苗,所有食物更被抢购一空。
美加收紧难民政策 未见曙光
挨过疫情,获确立为免遣返声请者,但Uzma一家仍未见曙光,近年接收滞港「难民」的美国和加拿大,皆收紧难民政策,无数家庭梦碎。
何处是「家」,对Uzma来说,或是终身的疑问。她形容,巴基斯坦是一个既快乐又不快乐的地方,因为是其出生地,充满儿时与家人相处的快乐回忆,但家人现已各散东西,只能透过电话联络。至于香港,她和家人居住多久也不会成为「香港居民」,只能视为「中途站」。
无数不确定性未有令Uzma停步,近两年,她加入基督教励行会工作,冀望以行动回馈,并以过来人的身份,为同样寻求庇护的群体带来安慰。她指,许多人对「难民」有误解,以为「难民」特意来港抢夺资源,背后或是身不由己,跟她一样有难以言喻的故事,「每个人都可被看见,被听见。」
回首过去,她没想到自己有如此强大的韧性,面对将来,她勇于与家人携手面对。她受邀到不同社群分享其生命故事,盼以生命影响生命,鼓励同路人保持信念,终会迎来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