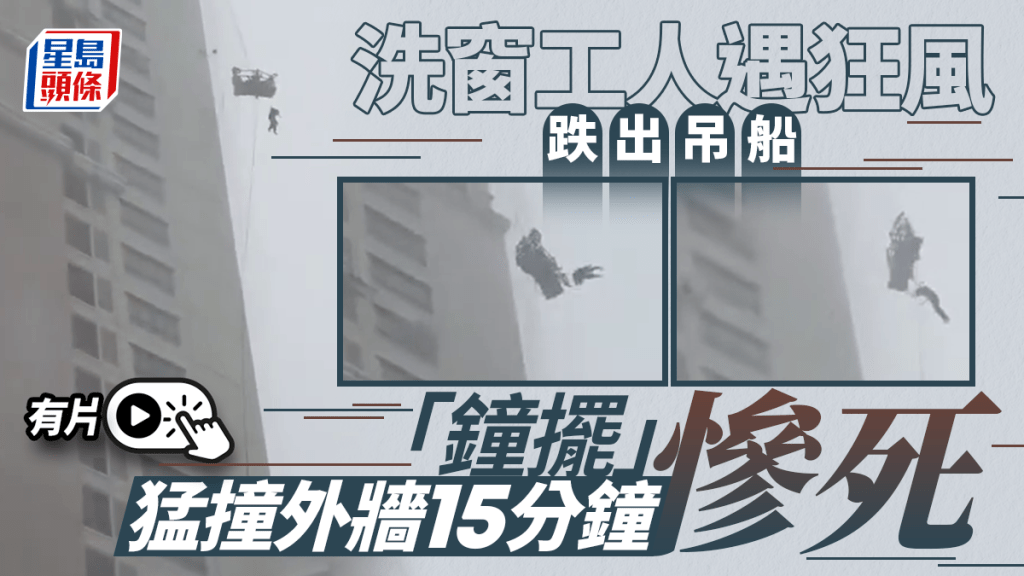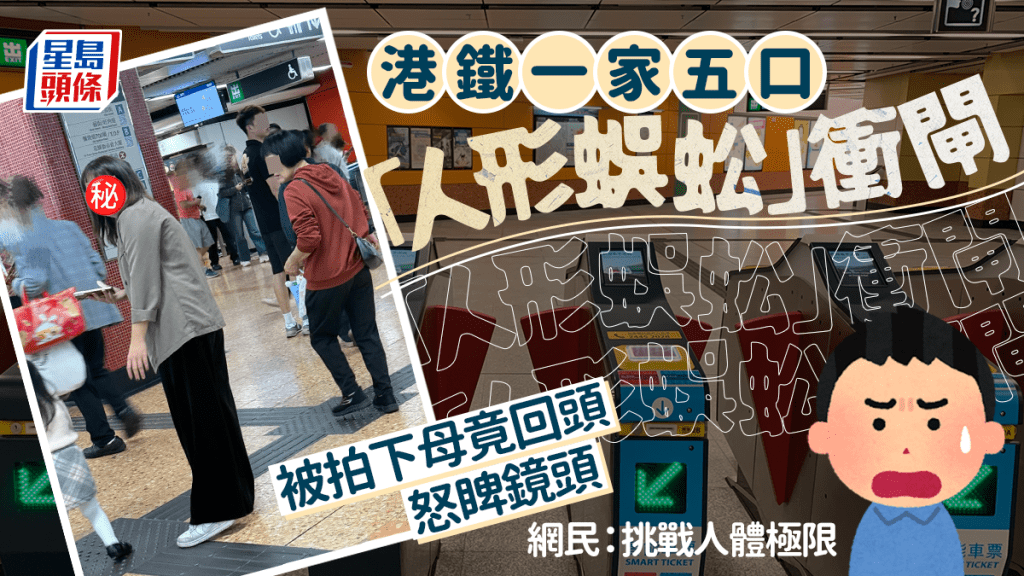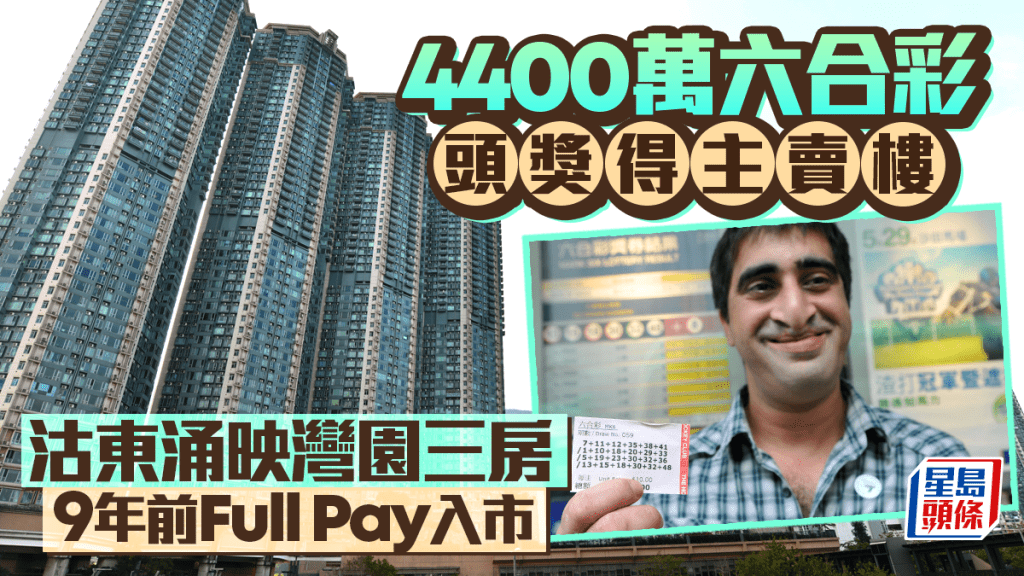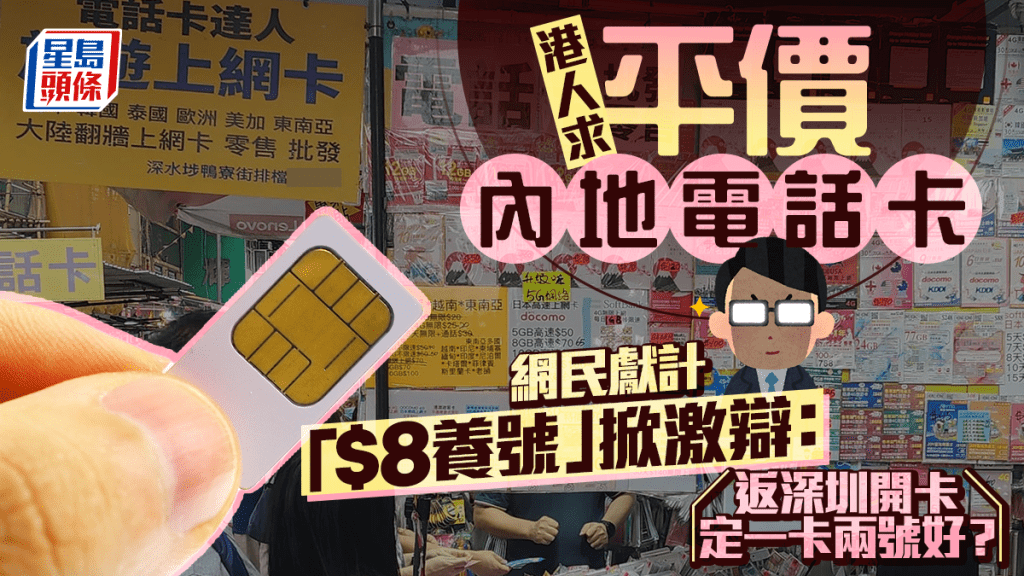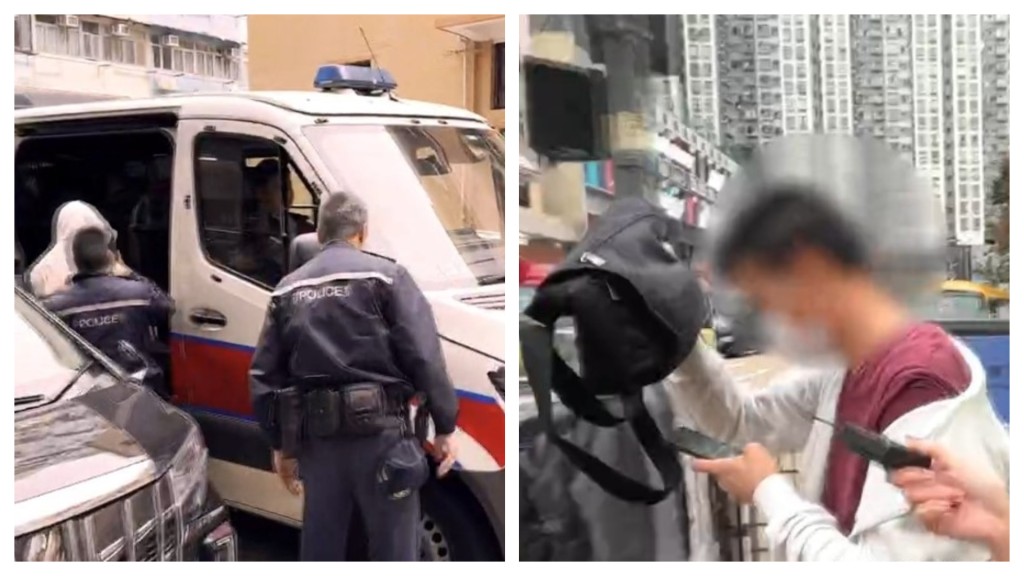非诚勿游——私藏和歌山

恐惧比瘟疫传播得更张狂,经过门堪罗雀的香港机场。屈指可数的乘客,口罩雨衣潜水面具出齐,众人面面相觑,踏进刑场一样的机舱。如坐针毡三个半小时的寂静机程,终见到脚下万家灯火的大阪暮色。
无论生活是如何的不堪,这里始终拥抱我。
无论命运如何背叛,我知道远方还有这岛。
冰冻失意的深夜,远方还有漫天坠落的绯红樱花。
落魄的当下,总是想起「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那种难舍难离的剪不断理还乱,非几十年的的亲身痴缠能够深切体会。
从三千日圆一晚的胶囊酒店、五千日圆的站前商务酒店,到两万日圆的一泊两食温泉旅馆。从一百日圆的原宿中古衫、青涩的涩谷潮牌,到十多万的银座订造西装,不论是周末小偷情还是环岛大约会,搭山手线返工到拍摄旅游节目,质与量的变化,竟然发生在一霎那。
就在那一霎那,舞象之年已知天命。一回首,那个乳臭未干的穷小子在昭和末年,寒窗苦读日文,平成初年混入富士同索尼,二十年青春职场人生与日本朝夕相对,是俺人生最长的春梦一场。
即使提前退休,即使瘟疫蔓延,封关前日本和歌山观光局仍诚邀我往当地,发掘一些人烟罕至的秘境抗疫景点,叫做My Secret Wakayama,我翻译成「私藏和歌山」。
「私」在日文中是第一身谦称,「藏」在日文中是隐藏,而「私藏」两字的中文语意亦暗合。
途中不知身是客,一晌总是贪欢。平成青年时最热衷于在东京出差开会之后,偷走出去和歌浦赏梅、黑潮泡温泉。令和时代仍旧本性难移,私藏的和歌山岁月固然静好,三天的拍摄采访瞬间完了,我还是赖死不走死缠烂打,因为强烈预感那扇半掩的障子户,快将关闭了。
项明生
无论生活是如何的不堪,这里始终拥抱我。
无论命运如何背叛,我知道远方还有这岛。
冰冻失意的深夜,远方还有漫天坠落的绯红樱花。
落魄的当下,总是想起「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那种难舍难离的剪不断理还乱,非几十年的的亲身痴缠能够深切体会。
从三千日圆一晚的胶囊酒店、五千日圆的站前商务酒店,到两万日圆的一泊两食温泉旅馆。从一百日圆的原宿中古衫、青涩的涩谷潮牌,到十多万的银座订造西装,不论是周末小偷情还是环岛大约会,搭山手线返工到拍摄旅游节目,质与量的变化,竟然发生在一霎那。
就在那一霎那,舞象之年已知天命。一回首,那个乳臭未干的穷小子在昭和末年,寒窗苦读日文,平成初年混入富士同索尼,二十年青春职场人生与日本朝夕相对,是俺人生最长的春梦一场。
即使提前退休,即使瘟疫蔓延,封关前日本和歌山观光局仍诚邀我往当地,发掘一些人烟罕至的秘境抗疫景点,叫做My Secret Wakayama,我翻译成「私藏和歌山」。
「私」在日文中是第一身谦称,「藏」在日文中是隐藏,而「私藏」两字的中文语意亦暗合。
途中不知身是客,一晌总是贪欢。平成青年时最热衷于在东京出差开会之后,偷走出去和歌浦赏梅、黑潮泡温泉。令和时代仍旧本性难移,私藏的和歌山岁月固然静好,三天的拍摄采访瞬间完了,我还是赖死不走死缠烂打,因为强烈预感那扇半掩的障子户,快将关闭了。
项明生
最Hit
汇丰180万客户仍持「红簿仔」 推现金奖鼓励过渡数码化 送999.9足金存折纪念品
2026-03-09 14:51 HKT
冯盈盈医生旧爱开专科诊所劲威水 另一港姐冠军惊喜到贺 钟文浩索妻颜值时刻在线
2026-03-09 10:00 HKT
港人求平价内地电话卡 网民献计「$8养号」掀激辩:返深圳开卡定一卡两号好?|Juicy叮
2026-03-09 12:59 H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