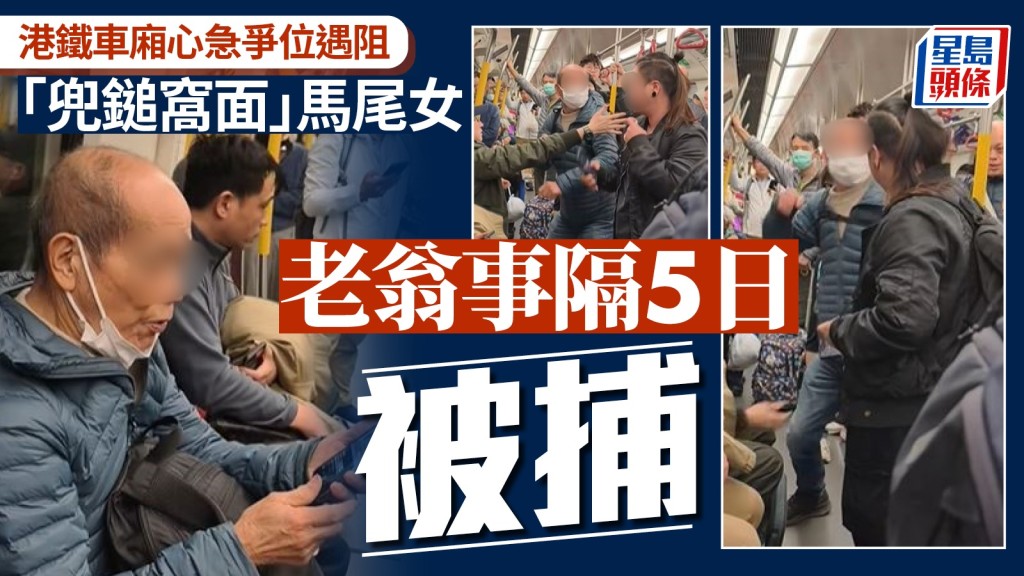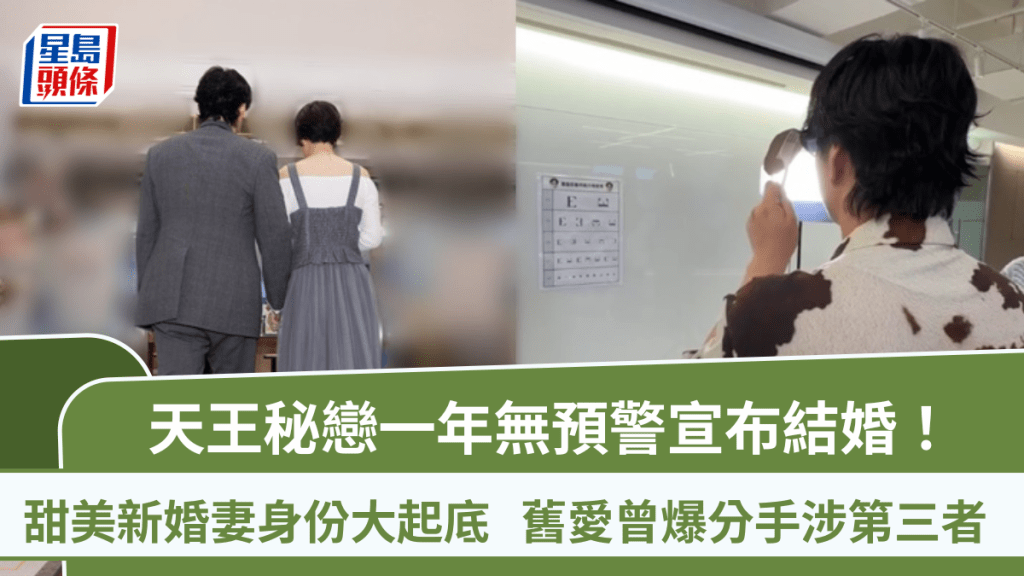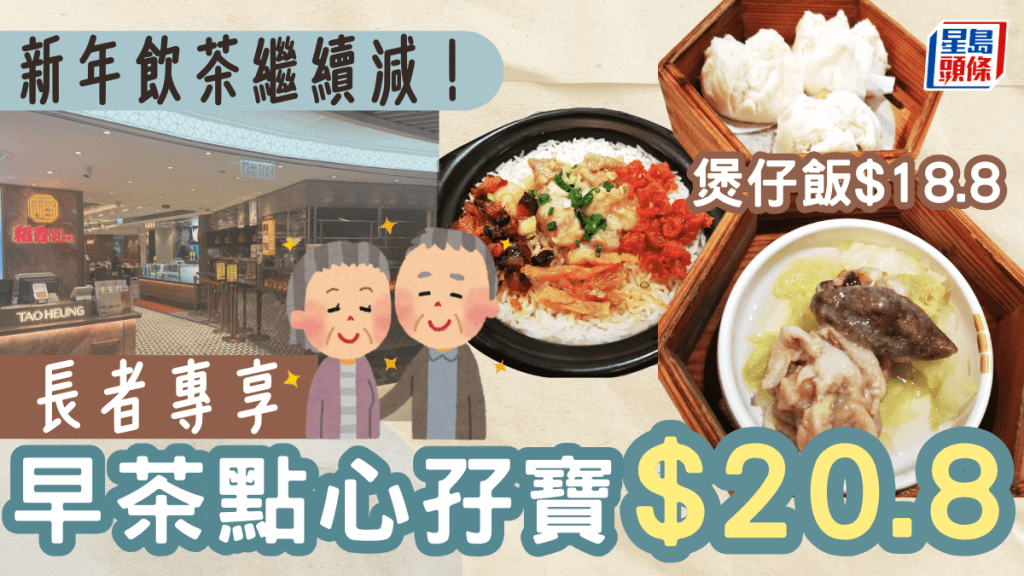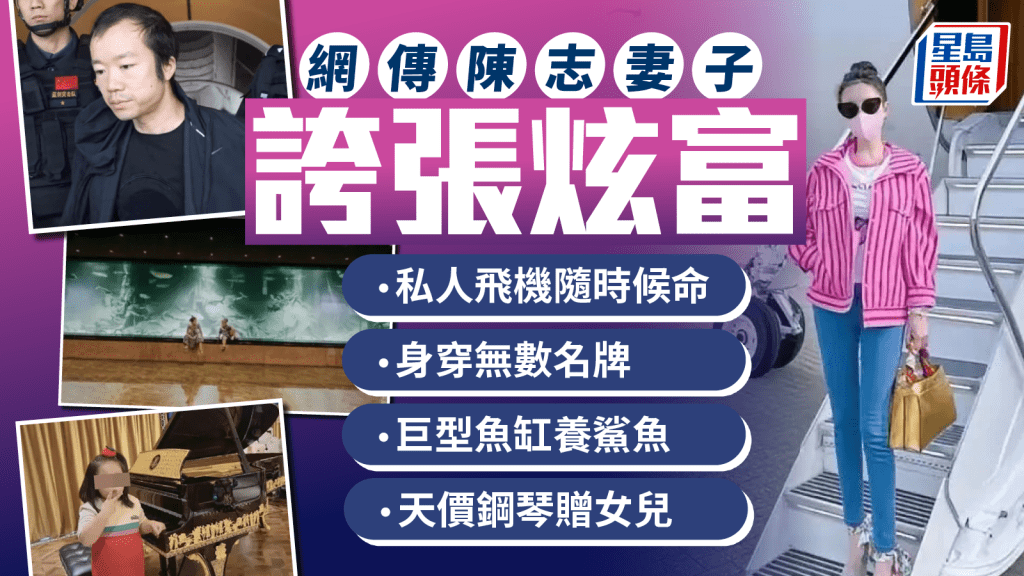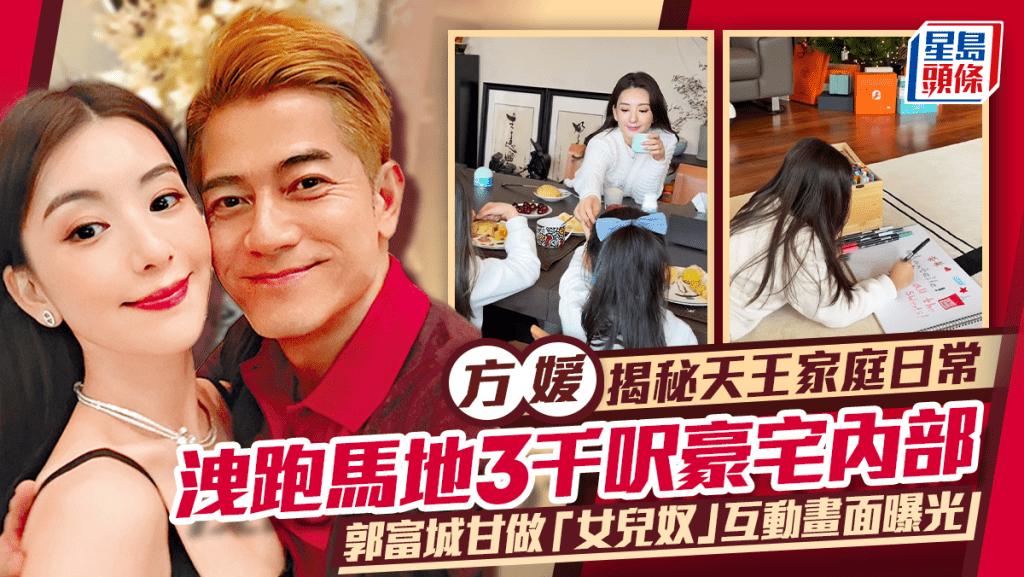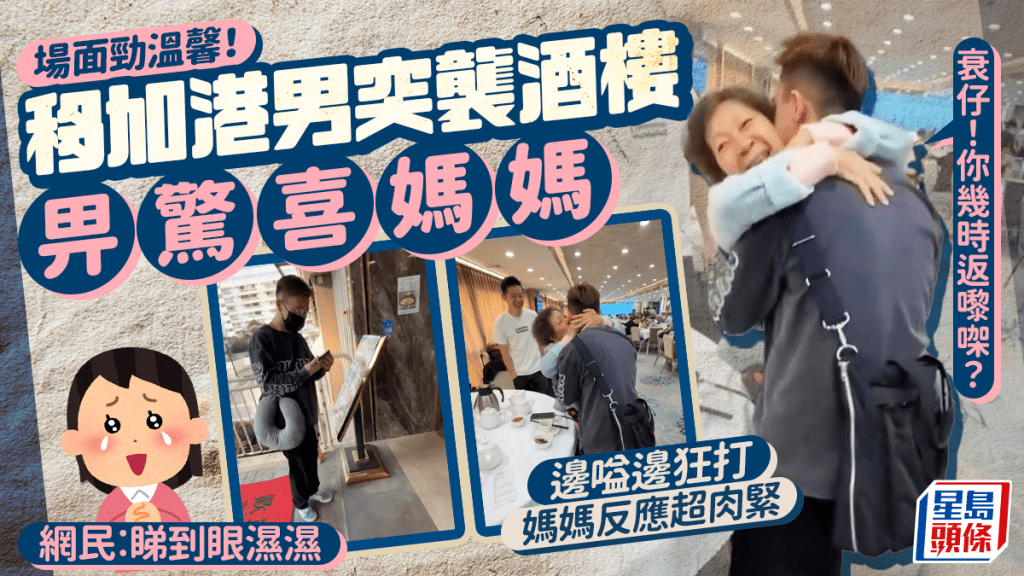陶杰 - 奥本海默 | 油尖多士

今年的奥斯卡大奖,无悬念颁给基斯杜化诺兰的电影《奥本海默》,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电影。
《奥本海默》不仅是一出足够份量的大电影,而且是可以与奥斯卡过去经典相提并论的作品,并非前几年一大堆,明显带有左派意识形态,专门为「身份政治」而宣传的电影。
《奥本海默》的选材,非艺高人胆大不能为,除了叙事手法和摄影,诺兰也懂得音乐来主导电影的节奏,而不是单纯的作为背景陪衬,这一点是继承了寇比力克。随音乐逐渐推进、紧张、增强,整个电影攀爬到最高潮的一幕,却突然寂静无声,效果震撼。
在TikTok世代,诺兰选择拍这样一部电影,探讨历史、政治、哲学。藉题发挥,抒发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他的野心是想将电影的叙事结构和拍摄手法还原到90年代,即美国知识分子制作兴盛的时期。
电影的开头曾掠过一系列名字:作曲家史特拉文斯基、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毕加索的立体派绘画,这些文艺作品典故,呈现在电影的开头,并非一般的抛书包(Name-dropping),虽然导演本身读的是英文系,但文学和历史知识丰富,这些作品不但显示其身处的时代浪潮,而且还成为主角心理精神的象征。
这些20世纪早期的文艺作品,都是在预告一个更加动荡暴力时代的降临,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变、导致社会阶层的冲突加剧,同时民族主义兴起,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战争规模,震撼世人的心灵,奥本海默因此登场。
奥本海默虽然是一个天才科学家,但是并不懂政治。在电影里,当时的科学家普遍左倾、反对核武,奥本海默也不例外,但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只知道一定要打败纳粹德国。赢取和平,代价艰巨,绝不只是喊口号,历史责任重于泰山,但在现实中只是由寥寥几个人肩负,《奥本海默》在这个时机推出,更是一部警世的作品。
前新闻工作者、多媒体社会评论人
陶杰
最H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