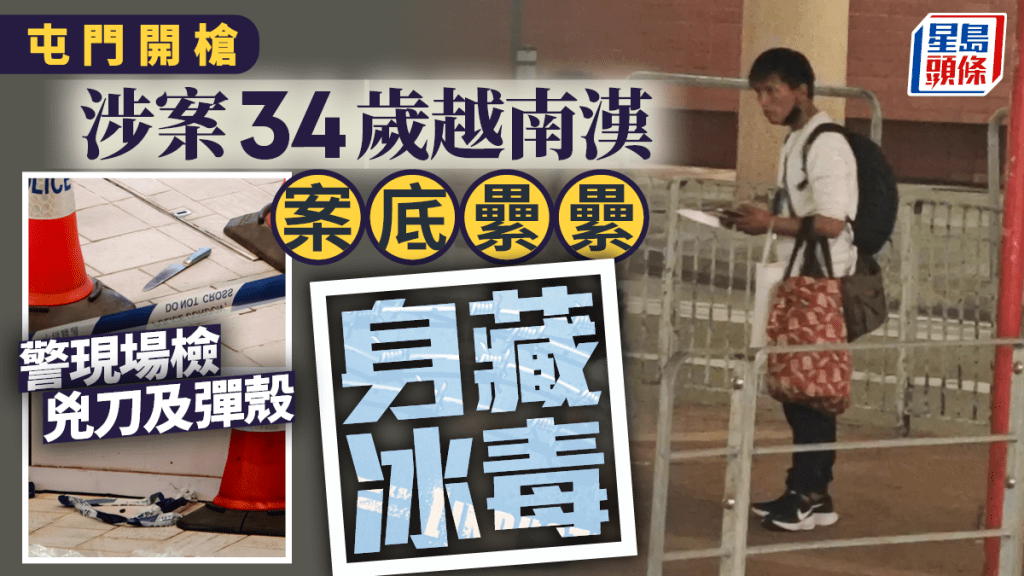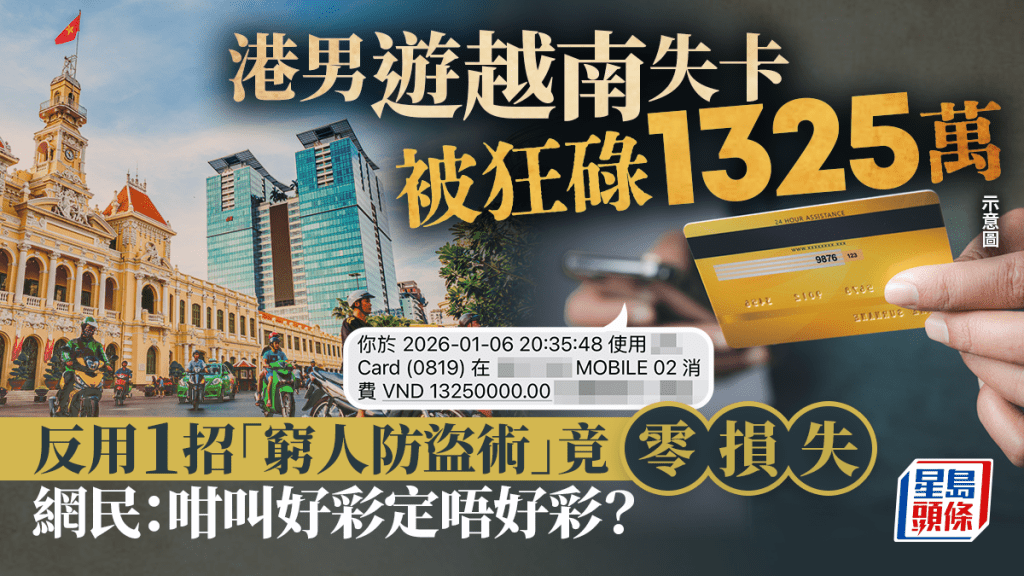卢永雄 - 泄密罪针对间谍而不是针对记者|巴士的点评

23条立法其中一个关注点,是窃取及泄露国家机密。其实现行的《官方机密条例》,已有一定条款规管窃取或泄露机密行为,今次立法是要将相关罪名重新整合修订。
窃密罪主要针对间谍而不是记者。如今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公然宣称要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而美国最近起诉一名中情局离职人员舒尔特,曝露中情局有一个入侵全球网络的黑客工具「宝库7号」(Vault 7),该前中情局人员,因泄露美国8761份机密文件,被判监40年。可见环球情报人员,都是竞相透过网上或实体入侵有其他政府的系统盗取机密,所以防范泄密变得特别重要。
新闻界关心23条立法,记者会不会因报道机密消息而获罪。可看看23条立法相关罪名,是「非法披露国家机密罪」,政府建议禁止任何人在没合法权限的情况下,非法披露国家秘密。
先看这个罪名的「犯罪行为」,包括:一,非法披露 ;二,披露的是国家机密。如记者以合法方式获取政府秘密,例如一个政府官员向记者吹风,就不涉及非法披露。
相反例子是若传媒贿赂公职人员获取政府机密资料再公布,那就是非法披露。例如《苹果日报》在1999年派记者花31万元,贿赂警察通讯员,获得999台的报警资料,最后涉案记者承认两项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囚10个月; 而涉案的两名警察通讯员亦分别被判囚7个月及9个月。
至于国家机密,新法例就有具体的定义,所以是否泄密,首先要确定泄露的是否国家机密。有传媒问报道外资大鳄沽空港元是不是泄密,这是一个市场行为,根本不是国家秘密。
至于「犯罪意图」,控方要证明泄露机密的人:a)明知相关资料属国家秘密;或(b)有合理因由相信资料属于国家秘密,并意图危害国家安全,而在没有合法权限下披露。换言之,一个人如果完全不知道某个资料属于国家秘密,也没理由相信披露会危害国家安全,便不算犯罪。
政府为求令传媒放心,正考虑加入「重大公众利益」的抗辩理由,虽然有法律界人士指维护国家安全与公众利益两个概念似有矛盾,而很多西方国家的《国安法》也并没有公众利益抗辩,但特区政府似乎依然想保留这一抗辩理由,令我想起亲身经历。
2002年11月,我从一个在内地医院工作的朋友处得知,广州开始流行一种不知名肺炎,几间医院收到大量类似病患,染病后恶化得很快,但当时未确定是否是一种新传染病。我当时任《星岛日报》总编辑,权衡后决定在报纸头版报道。我并不知官方对这一疾病的态度,另外,亦觉得报道有助公众预防,所以最终决定报道。其实这是则环球独家新闻,因为这种疾病就是后来确认的SARS。
如用现行建议中的法例,我当时报道这种新的流行病并不违法,因为我既不是非法获取讯息,有关消息没跌入国家机密范畴,因它只是一个医院的流行病,而不是国家重大决策。我亦无犯罪意图,即使国家当时已在研究这种疾病,但我并不知情,所以非明知其是国家机密而报道。当然最后我也有「重大公众利益」抗辩,因为提醒公众防止严重的传染病流行,应属重大公众利益。
保守国家机密的法例,自然会减少消息传播的自由,因为真的不可以非法披露会损害国家安全的国家机密,但关键是新法例是否可以做到在保障自由与国家安全中,取得合理平衡。
「巴士的报」是一份网上报纸,让网民随时随地
拿着手机或平板电脑可以看到。
www.bastillepost.com
卢永雄